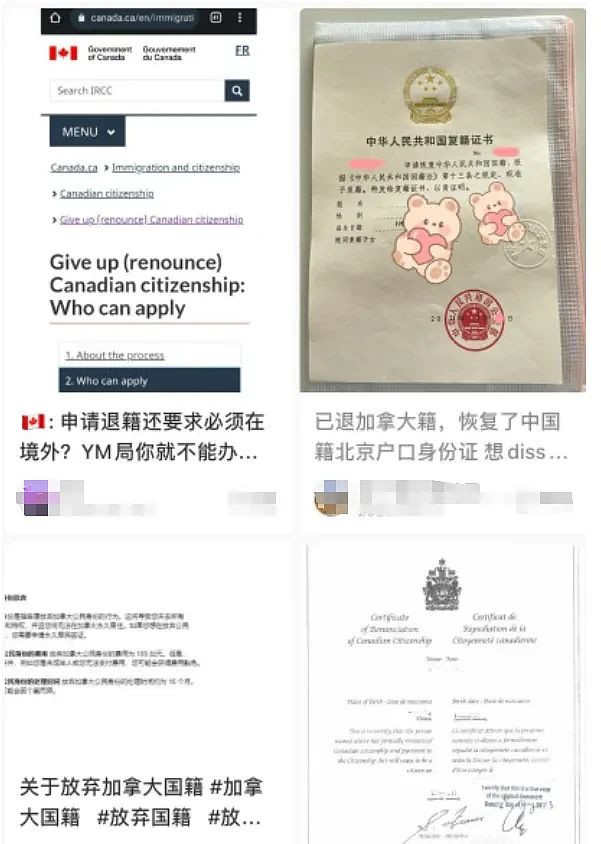返京路上发烧,我在火车站被120带走,还好一场虚惊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始料未及的春节,武汉人感受尤为深刻。因一场疫情而起的紧张、无措、悲伤、奋斗、驰援和奉献,雕刻了光阴。我们此刻所有的经历和记录,都将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一位北漂青年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还乡和返程经历,整个假期他去了三次医院,甚至曾在火车站被120拉走,好在最后都是虚惊一场。以下是他的自述。
回老家的头一天,我看着车窗外的夕阳,感慨着北京的冬天真美。
1月21日,是我年前回老家的日子。我一早起来便准备好行李带到了公司,想着下班后直接去高铁站。因为这段时间身体不好,之前得了急性荨麻疹,后来又感冒,我出门时特地带上了体温计,上班期间也一直戴着口罩。
当天公司要求员工填写个人身体状况的调查,我拿到表格,看到“是否接触过武汉来京人员”这一项,突然想起10天前刚刚见过一位武汉来的朋友。我们久未碰面,聊得很愉快,我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十六,月亮又大又圆。
我赶紧量了一下体温:37.5度。那一刻,我慌了。
摄影/蒋磊磊 编辑/王漠沙
我询问了那位武汉的好友,他表示身体一切安好。我稍微安下了心,但还是保持了警惕。下班后,我没有乘坐公共交通,打车到了高铁站,也一直戴着口罩。
高铁车厢里满满当当,只有极少数的乘客戴着口罩。有位中年男子一直在咳嗽,没戴口罩也没有遮挡,这着实让我有些困扰。我走过去送了他一个口罩,他一直戴着直到下车。
我爸妈在西安开餐馆。晚上10点,我在西安站下车,和爸妈汇合,计划着一起回汉中老家。见面后,我特地让他们与我保持距离,减少交谈。他们觉得我有些小题大做了。
夜里,我联系了一位在西安的医生朋友,他建议我第二天一早去医院做个排查。第二天一早,我谢绝了母亲的陪同,一个人去了医院。那位医生朋友根据当时下发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案中的要求,给我做了检查。抽血化验和胸部透视都未见异常,这下我才真的放了心。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父母和几个同事。虽然前一天在公司里,他们都很友善地保持着克制,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大家的忧虑。我的同事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面对疫情,不得不再三谨慎小心。
夜里,我联系了一位在西安的医生朋友,他建议我第二天一早去医院做个排查。第二天一早,我谢绝了母亲的陪同,一个人去了医院。那位医生朋友根据当时下发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案中的要求,给我做了检查。抽血化验和胸部透视都未见异常,这下我才真的放了心。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父母和几个同事。虽然前一天在公司里,他们都很友善地保持着克制,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大家的忧虑。我的同事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面对疫情,不得不再三谨慎小心。
从北京、西安到汉中城区再到乡镇,人们对疫情的警惕滑坡式的衰弱。面对老家不愿意戴口罩还要到处串门的长辈们,我有些无所适从。我和几个同辈每天都疯狂往家族群里甩疫情相关的链接,但作用并不大。
每年除夕夜,家里人都要给财神爷烧纸,我们家有个说法,烧的纸灰飘的越高、越多,来年就会越旺。
大年三十整个晚上我一直在围着火炉吃火锅,这是我第一次在除夕夜没有看一眼春晚。我的心思除了过年,还有一大半仍然在关注着疫情,尤其是我还有一位好朋友在武汉。我的心情在过年和为疫情焦虑之间来回切换。
第二天,如往年一样,我被迎神的鞭炮惊醒。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人都要去庙里祈福,这次去的庙在深山里,结构奇特,进入主殿之前要钻过一个溶洞。
我们的车开到山脚下,剩下的路只能徒步。父亲和姐姐、姐夫走在前面,母亲在山路上走走停停,我没想到爬这样的山对她来说已经开始有些吃力了,岁月真的不饶人。
过年来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家里的每个人求“一条红”。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年后返校,母亲都会给我塞包里,我觉得很难看、丢人。这几年工作了,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在一起,这才慢慢明白,这条红里寄托了家人的美好祝福和思念。所以这几年,我对这件事,也多了些敬畏和理解。
大年初二,附近市县的疫情传闻开始在家族群中传开。村里的人渐渐开始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天本该是姑姑们回娘家看望我爷爷的日子,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决定等疫情过后再回来。
每天吃过午饭,我便带着外甥女和几个同辈去田里跑步。两个外甥女在乡下玩得很开心,姐姐一直说如果留在市区哪也不能去,两个小孩一定会憋坏了。一到晚上,孩子们开始放烟花、吹泡泡,母亲也跟着她们一起玩起来,开心地像个孩子。
后面几天,家里的零食都吃光了,姐姐开车带我去街上买东西。我才发现各个乡镇都已经在路口设置了检测点,外地车主体温正常才能出入,街上也开始变得萧条了。
我回京的前一天下午,母亲接到舅妈打来的电话,虽然没听清对方说什么,但是看到母亲的神色,我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前两天还好好的二姥姥突然摔了一跤突发脑溢血昏迷了,被拉去了县医院,县医院收治不了,接着又转院去了是市区的三甲医院。而这两家医院都已经被规划为汉中市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院。
当天二姥姥家的晚辈们十几个人全都去了医院,在担心二姥姥安危的同时,对于疫情的恐惧也涌了上来。
回老家的第二天,我拍下了二姥姥家院子里晒的鱼头。当时她问我,拍鱼头干什么,我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答。
二姥姥出事后,本来全都在医院里的亲戚考虑到不能把二姥爷独自留在家里,于是便让一拨人回到了家里。而另一拨留在医院的人一时半会也不能出来,因为医院当时已经收治了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留在医院的人要隔离一周才可以离开。
二姥姥的情况很不乐观,医生叮嘱家属要准备好后事。父亲从医院回来后,和村里二十多个人开始在地里修墓,母亲在厨房帮忙做饭,而我也只能干着急,在担心二姥姥病情的同时,也不停地叮嘱父母要做好防护。
返程那天,爷爷站在路边与我道别。
正月初五,我回京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了各处都加强了对疫情的防控,高铁进站口防疫人员全副武装,体温正常才可以进站。高铁上也几乎没什么人。
汉中站。
一路上昏昏沉沉,我除了玩手机就是睡觉。傍晚六点左右,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列车员的声音:“你们是从湖北来的吗?”我一下惊醒了,本能地竖起耳朵听着列车员询问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一家三口。原来那家的男主人籍贯在湖北,但是户口在北京,他们过年是去了女方河南老家。
列车员走后我听到那个女子趴在男人耳边笑着说,“刚才一听说你是武汉的,后面的人全都醒了”,听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害臊。
列车员为湖北一家人量体温。
到了晚上八点半,列车员开始给所有乘客量体温,填个人信息。到我前面五排的时候,一个女乘客体温37.5,车厢里的人都紧张了起来。列车员又给她量了一次,还是37.5,只好给上级通报。而到我的时候,体温枪响起了哔的一声——
列车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怎么回事?”
我也愣了:“我怎么了?”
接着列车员对着传呼机说:“这又一个发烧的,37.6!”
列车员留下还在发愣的我,继续给后面的乘客测量,到最后一排的时候,列车员大叫:“这节车厢怎么回事,又一个发烧的,37.3!”
信息登记表和我自己量的体温,当时我自己测量只有37度。
后来列车员反复给我们三个确认体温情况,态度也很好,边量边说,“我希望你们都没事,一切正常,不然会很麻烦”。最后,另外两个人都被排除了,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发烧,列车员便把我这节车厢的其他乘客全部疏散到了隔壁车厢,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点慌,有点愣,有点孤立无援。我开始胡思乱想,我会被隔离吗?会确诊吗?会把我拉到哪家医院?要不要通知家人?什么时候通知呢?
信息登记表和我自己量的体温,当时我自己测量只有37度。
后来列车员反复给我们三个确认体温情况,态度也很好,边量边说,“我希望你们都没事,一切正常,不然会很麻烦”。最后,另外两个人都被排除了,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发烧,列车员便把我这节车厢的其他乘客全部疏散到了隔壁车厢,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点慌,有点愣,有点孤立无援。我开始胡思乱想,我会被隔离吗?会确诊吗?会把我拉到哪家医院?要不要通知家人?什么时候通知呢?
车厢被清空。
还没等我想出答案,刚才量体温的列车员便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地来到我旁边。
北京西站工作人员前来交接。
九点半,到达北京西站后,列车员联系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了隔离点。在工作人员的对话中,我隐约听到他们正在叫120,要等一会才能到。
这一等,就到了十一点多。期间母亲还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心情很差,很不耐烦地聊了两句我就挂了,说自己已经到家,准备休息。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热的事情,免得他们担心干着急。
我在隔离点,不敢坐椅子上,就在这里站了一个多小时。
11点多,终于有了动静,西站工作人员带着我往站外走,一直走到一辆120旁。这是我第一次坐救护车,除了紧张,还有点好奇和激动。
救护车内部。
下车后我问带路的工作人员:“隔离的地方是单间吗?我怕交叉感染。”
去发热门诊的路上。
到了医院,拐来拐去终于到了发热门诊,还有几个病人在问诊。工作人员等在门外,并让门诊的人都先出来,接着我才拖着行李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了一种回到人间的感觉,心突然平静了下来。
挂完号,医生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做了几项检查。不到半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医生表示我什么事都没有。
医生问我:“120掏钱了吗?”我说:“没有”,他回道:“那挺好的。”
第二天睡醒后,我把那一夜的经历告诉了姐姐,并叮嘱她不要跟爸妈讲。她说,汉中从市区到乡镇的防疫工作都升级了,很多地方没有通行证不能通过,我们村口也设起了路障。她有一种要逃难,但是又无路可逃的感觉。
这段时间我仍然在家中隔离,每天量体温。北京西站、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局的工作人员轮番给我打电话,不断确认我返京那天的过程,并问我有没有每天量体温,体温是多少。
正月十五那天,我收到家里的最新消息,二姥姥的病情好转,已经可以活动了。
傍晚,窗外有人放起来了烟火,夜幕下格外好看。看着这景色,回想着这个年发生的一切,我突然释然了。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