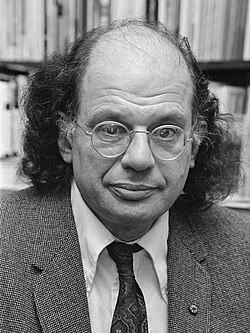早年生活与家庭
金斯伯格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犹太[17]家庭,并在附近的帕特森长大。[18] 他是父亲路易斯·金斯伯格的次子,父亲也出生于纽瓦克,是一位教师和出版诗人;母亲原名娜奥米·利维,出生于俄罗斯涅韦尔,是一位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19]
青少年时期,金斯伯格开始给《纽约时报》写信,探讨政治问题,例如二战和工人权利。[20] 他在《帕特森晨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21] 高中时期,受老师热情洋溢的朗读启发,金斯伯格对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产生了兴趣。[22] 1943年,金斯伯格从东区高中毕业,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学院短暂就读,之后凭借帕特森青年希伯来协会的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金斯伯格原本打算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但后来改主修文学。[19]
1945年,他加入商船队,以赚取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的学费。[23]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金斯伯格为文学期刊《哥伦比亚评论》和幽默杂志《小丑》撰稿,荣获伍德伯里诗歌奖,担任爱乐协会(文学和辩论团体)主席,并加入了野猪头协会(诗歌协会)。[22][24] 他住在哈特利楼,杰克·凯鲁亚克和赫伯特·戈尔德等“垮掉的一代”诗人也曾居住于此。[25][26] 金斯伯格曾表示,他最喜欢的哥伦比亚大学课程是大学一年级必修的“伟大著作”(由莱昂内尔·特里林讲授)。1948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得英语和美国文学学士学位。[27]
据诗歌基金会称,金斯伯格在一次听证会上声称自己精神错乱,随后在精神病院待了几个月。据称,他因在宿舍藏匿赃物而被起诉。据称,被盗财物并非金斯伯格所有,而是属于一位熟人的。[28] 金斯伯格还参加了鲍厄里圣公会圣马可教堂的公开朗诵会,该教堂后来在他去世后为他举行了追悼会。[29][30]
与父母的关系
金斯伯格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称他的父母是“老式的熟食店哲学家”。[18] 他的母亲也是一名活跃的共产党员,经常带金斯伯格和他的弟弟尤金参加党的会议。金斯伯格后来回忆说,他的母亲“编造的睡前故事都大体是这样的:‘善良的国王骑马从城堡里出来,看到受苦的工人,并治愈了他们。’”[20] 谈到他的父亲,金斯伯格说道:“我的父亲会在家里走来走去,要么低声吟诵艾米莉·狄金森和朗费罗的作品,要么攻击T·S·艾略特用他的‘蒙昧主义’毁掉了诗歌。我对这两种说法都产生了怀疑。”[18]
金斯伯格的母亲娜奥米·金斯伯格患有精神分裂症,其症状常常表现为偏执妄想、思维紊乱和多次自杀未遂。[31] 例如,她会声称总统在家里植入了窃听器,而她的婆婆正试图杀死她。[32][33]娜奥米对周围人的怀疑,导致她与年幼的艾伦(比尔·摩根在其金斯伯格传记《我庆祝自己:艾伦·金斯伯格的某种私人生活》中称之为“她的小宠物”)的关系更加密切。[34] 她还试图割腕自杀,不久后被送往格雷斯通精神病院;金斯伯格的大部分青春岁月都在精神病院度过。[35][36] 他与母亲以及母亲精神疾病的经历,是他创作两部主要作品《嚎叫》和长篇自传体诗《献给娜奥米·金斯伯格的卡迪什(1894-1956)》的主要灵感来源。[37]
初中时,他陪母亲乘公共汽车去看心理医生。这次旅行深深地困扰着金斯伯格——他在《卡迪什》中提到了这次旅行以及童年时期的其他时刻。[38] 他与母亲的精神疾病以及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经历,在《嚎叫》中也多次被提及。例如,“朝圣者州立、罗克兰和灰石的恶臭大厅”指的是他母亲和卡尔·所罗门经常光顾的机构,而这首诗表面上是这首诗的主题:纽约州的朝圣者州立医院和罗克兰州立医院,以及新泽西州的灰石公园精神病院。[34][39][40] 紧接着是“母亲终于******”这句话。金斯伯格后来承认,删除的是脏话“操”。[39] 他在第三部分还提到所罗门:“我和你一起在罗克兰,你模仿我母亲的影子”,再次表明了所罗门和他母亲之间的联系。[41]
金斯伯格在母亲去世后收到了一封回信,回信是他寄给她的《嚎叫》的副本。信中告诫金斯伯格要乖乖听话,远离毒品;她说:“钥匙在窗户上,钥匙在窗户的阳光里——我有钥匙——艾伦,结婚吧,别吸毒——钥匙在酒吧里,在窗户的阳光里。”
在她写给金斯伯格弟弟尤金的信中,她写道:“上帝的线人来到我的床边,我在天空中看到了上帝本人。阳光也照耀着我,一把钥匙挂在窗户边,让我可以出去。阳光的黄色也照亮了窗户边的钥匙。”[43] 这些信件以及缺乏诵读卡迪什(Kaddish)的设施,激发了金斯伯格创作《卡迪什》(Kaddish)。其中引用了娜奥米生活中的许多细节、金斯伯格与她相处的经历以及这封信,包括“钥匙在光明中”和“钥匙在窗户里”这两句话。[44]
纽约节拍
本节需要更多引文以作核实。请在此部分添加可靠来源的引文,以帮助我们改进本文。未注明来源的材料可能会受到质疑和删除。 (2024年8月)(了解如何以及何时删除此消息)
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年结识了本科同学卢西安·卡尔,后者将他介绍给了多位未来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包括杰克·凯鲁亚克、威廉·S·巴勒斯和约翰·克莱伦·霍姆斯。他们之所以结缘,是因为他们彼此都看到了对美国青年潜力的热情,这种潜力超越了二战后麦卡锡时代美国严格的墨守成规。[45] 金斯伯格和卡尔激动地谈论着对文学和美国的“新视野”(这一短语改编自叶芝的《一个视野》)。卡尔还将金斯伯格介绍给了尼尔·卡萨迪,金斯伯格对他一直心存迷恋。[46] 凯鲁亚克在其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的第一章中描述了金斯伯格和卡萨迪的相遇。[38]凯鲁亚克将他们视为“新视野”中阴暗的一面(金斯伯格),光明的一面(卡萨迪)。这种看法部分源于金斯伯格与共产主义的联系,而凯鲁亚克对共产主义的怀疑日益加深。尽管金斯伯格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但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中称他为“卡洛·马克思”。这成为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22]
此外,在纽约,金斯伯格在小马厩酒吧遇到了格雷戈里·科索。科索当时刚从监狱获释,得到了小马厩酒吧顾客的支持,并在他们见面的当晚在那里写诗。金斯伯格声称,他立刻就被科索吸引,科索是异性恋,但在监狱服刑三年后,他理解了同性恋。金斯伯格在阅读科索的诗歌时更加震惊,意识到科索“精神上天赋异禀”。金斯伯格把科索介绍给了他其他的核心圈子。在马厩的第一次见面中,科索给金斯伯格看了一首诗,诗中描绘的是一位住在他街对面、在窗边裸体晒太阳的女子。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女子恰好是金斯伯格的女友,金斯伯格在一次异性恋尝试中与她同居。金斯伯格把科索带到了他们的公寓。在那里,这位女子向年纪尚轻的科索求爱,科索害怕地逃走了。金斯伯格把科索介绍给了凯鲁亚克和巴勒斯,他们开始一起旅行。金斯伯格和科索成为了终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47][需要更多引文]
在金斯伯格人生的这段时期结束后不久,他通过巴纳德学院的哲学教授亚历克斯·格里尔认识了艾丽丝·纳达·考恩,并与之发展了一段恋情。亚历克斯·格里尔在“垮掉的一代”蓬勃发展的时期曾与金斯伯格交往过一段时间。在巴纳德学院读书期间,艾丽丝·考恩广泛阅读了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的诗歌,并结识了乔伊斯·约翰逊、利奥·斯基尔等“垮掉派”诗人。[引文需要]考恩大部分时间都对较为阴暗的诗歌情有独钟,而“垮掉派”诗歌似乎也为她提供了某种魅力,让她得以窥见人格中阴暗的一面。在巴纳德学院期间,考恩加入了一个由反建制艺术家和空想家组成的小团体,外人称之为“垮掉的一代”,因此获得了“垮掉的爱丽丝”的绰号。她在学院最早认识的一位朋友是“垮掉的一代”诗人乔伊斯·约翰逊,后者后来在她的著作中刻画了考恩的形象,包括《次要人物》和《来跳舞吧》,这两本书分别讲述了两位女性在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垮掉的一代”群体中的经历。[引文需要]通过与艾丽丝·考恩的交往,金斯伯格发现他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卡尔·所罗门,后来他把自己最著名的诗歌《嚎叫》献给了他。这首诗被认为是金斯伯格 1955 年之前的自传,并通过他与当时其他垮掉的一代艺术家的关系,简要介绍了垮掉的一代的历史。
“布莱克幻觉”
1948年,金斯伯格在东哈莱姆区的一间公寓里,一边自慰一边阅读威廉·布莱克的诗歌,突然出现了幻听[48],他后来称之为“布莱克幻觉”。金斯伯格声称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也被描述为“亘古常在者的声音”——或者布莱克本人朗读《啊!向日葵》、《病玫瑰》和《迷失的小女孩》。这种体验持续了数天,他相信自己见证了宇宙的互联互通;金斯伯格回忆说,在看了公寓消防梯上的格子结构,然后又看了看天空后,他直觉地认为其中一个是人类制造的,而另一个是他自己制造的。[49] 他解释说,这种幻觉并非由吸毒引起,而是他后来试图用各种药物来重拾那种互联互通的感觉。[22]后来,在1955年,他在诗歌《向日葵经》中提到了他的“布莱克幻象”,写道:“——我如痴如醉地冲上前去——这是我的第一朵向日葵,关于布莱克的回忆——我的幻象——”。[50]
旧金山文艺复兴
金斯伯格于20世纪50年代移居旧金山。在1956年《嚎叫及其他诗歌》由城市之光出版社出版之前,他曾担任市场研究员。[51]
1954年,金斯伯格在旧金山结识了彼得·奥洛夫斯基(1933-2010),并爱上了他,后者成为了他的终身伴侣。[22]他们的通信选段已经出版。[52]
同样在旧金山,金斯伯格结识了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员(詹姆斯·布劳顿、罗伯特·邓肯、玛德琳·格里森和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以及其他后来被广泛归类为“垮掉的一代”的诗人。金斯伯格的导师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给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军人物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写了一封介绍信,后者随后将金斯伯格引入了旧金山诗坛。[53] 在那里,金斯伯格还结识了三位在里德学院结识的崭露头角的诗人和禅宗爱好者:加里·斯奈德、菲利普·惠伦和卢·韦尔奇。1959年,金斯伯格与诗人约翰·凯利、鲍勃·考夫曼、A·D·维南斯和威廉·马戈利斯共同创办了诗歌杂志《福祉》(Beatitude)。
1955年中期,画家兼六画廊联合创始人沃利·赫德里克找到金斯伯格,请他在六画廊组织一场诗歌朗诵会。起初,金斯伯格拒绝了,但当他写完《嚎叫》的草稿后,用他的话说,他“他妈的改变了主意”。[45]金斯伯格将活动宣传为“六位诗人在六画廊”。“垮掉的一代”神话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简称为“六画廊朗诵会”,于1955年10月7日举行。[54]这场活动本质上汇集了东西海岸“垮掉的一代”的现实情况。对金斯伯格个人而言,当晚的朗诵会更有意义,其中包括《嚎叫》的首次公开朗诵,这首诗为金斯伯格以及与他相关的许多诗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中描述了那晚的情景,描述了人们如何从观众那里收集零钱来买酒,以及金斯伯格如何张开双臂,激情洋溢、醉醺醺地朗读。
金斯伯格里程碑式诗集《嚎叫及其他诗歌》(1956)初版封面
金斯伯格的主要作品《嚎叫》以其开篇之语而闻名:“我看到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思想被疯狂摧毁,饥饿、歇斯底里、赤身裸体……”。《嚎叫》在出版时因其粗俗的语言而被认为是丑闻。1956年,它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出版后不久,就因涉嫌淫秽而被禁。这项禁令在《第一修正案》的捍卫者中引起了轰动,后来,在克莱顿·W·霍恩法官宣布这首诗具有可取的艺术价值后,禁令得以解除。[22]金斯伯格和因贩卖《嚎叫》而入狱的城市之光乐队经理 Shig Murao 成为了终生的朋友。[55]
《嚎叫》中的传记引用
金斯伯格曾声称,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部延伸的传记(就像凯鲁亚克的《杜洛兹传奇》一样)。《嚎叫》不仅是金斯伯格1955年之前经历的传记,也是一部“垮掉的一代”的历史。金斯伯格后来还声称,《嚎叫》的核心是他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未解决的情感。尽管《卡迪什》更明确地描写了他的母亲,但《嚎叫》在很多方面也受到了同样的情感驱动。《嚎叫》记录了金斯伯格一生中许多重要友谊的发展。这首诗的开头是“我目睹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思想被疯狂摧毁”,这为金斯伯格描写卡萨迪和所罗门奠定了基础,并将他们永垂不朽地载入美国文学。[45]这种疯狂是社会运转所需的“愤怒的解药”——疯狂是它的疾病。在诗中,金斯伯格聚焦于“卡尔·所罗门!我与你同在罗克兰”,从而将所罗门塑造成一个寻求摆脱“束缚”的典型人物。尽管他大部分诗歌中的引用都揭示了他的生平、他与其他“垮掉的一代”成员的关系以及他自身的政治观点,但他最著名的诗歌《嚎叫》或许仍然是最好的起点。[需要引用]
去巴黎和“垮掉的一代”旅馆,丹吉尔和印度
1957年,金斯伯格离开旧金山,震惊了文坛。在摩洛哥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和彼得·奥洛夫斯基在巴黎加入了格雷戈里·科尔索的行列。科尔索把他们介绍到吉特勒-科乌尔街9号一家酒吧楼上的一间破旧的寄宿公寓,后来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旅馆。很快,巴勒斯等人也加入了他们。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段富有成效、充满创造力的时光。在那里,金斯堡开始创作他的史诗《卡迪什》(Kaddish),科尔索创作了《炸弹与婚姻》(Bomb and Marriage),而巴勒斯(在金斯堡和科尔索的帮助下)则将之前的作品整合成《裸体午餐》(Naked Lunch)。这段时期被摄影师哈罗德·查普曼记录下来。他大约在同一时期搬进了这家“旅馆”,并不断拍摄旅馆里的住户,直到1963年旅馆关闭。1962年至1963年间,金斯堡和奥尔洛夫斯基游历了印度各地,在加尔各答(现加尔各答)和贝拿勒斯(瓦拉纳西)各住半年。在前往印度的途中,他在雅典停留了两个月(1961年8月29日至1961年10月31日),期间他参观了德尔斐、米奇内斯、克里特岛等地,然后继续他的旅程,前往以色列、肯尼亚,最终抵达印度。[56]在此期间,他还与当时一些杰出的孟加拉青年诗人建立了友谊,其中包括沙克蒂·查托帕迪亚伊(Shakti Chattopadhyay)和苏尼尔·甘戈帕迪亚伊(Sunil Gangopadhyay)。金斯伯格在印度拥有多位政界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普尔·贾亚卡尔(Pupul Jayakar),在当局急于驱逐他时,他帮助金斯伯格延长了在印度的居留时间。
英国与国际诗歌的化身
1965年5月,金斯伯格抵达伦敦,并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免费朗诵他的诗歌。[57]抵达后不久,他在“更好的书店”(Better Books)举办了一场朗诵会。杰夫·纳托尔(Jeff Nuttall)称其为“给饱受摧残的集体心灵带来的第一阵治愈之风”。[57] 汤姆·麦格拉斯(Tom McGrath)写道:“这很可能成为英国历史上——或者至少是英国诗歌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书店朗诵会结束后不久,国际诗歌化身活动[58]的计划就已酝酿,该活动于1965年6月11日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活动吸引了7000名观众,他们聆听了包括金斯伯格、阿德里安·米切尔、亚历山大·特罗基、哈里·费恩莱特、安瑟姆·霍洛、克里斯托弗·洛格、乔治·麦克白、格雷戈里·科索、劳伦斯·费林盖蒂、迈克尔·霍洛维茨、西蒙·文肯诺格、斯派克·霍金斯和汤姆·麦格拉斯在内的众多名人的朗诵、现场和录音表演。此次活动由金斯伯格的好友、电影制片人芭芭拉·鲁宾组织。[59][60]
彼得·怀特黑德用胶片记录了此次活动,并将其命名为《完全共融》(Wholly Communion)。英国的洛里默出版社和美国的格罗夫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同名书籍,其中包含电影中的图片和一些当时表演的诗歌。
持续的文学活动
金斯伯格与他的伴侣、诗人彼得·奥洛夫斯基。照片拍摄于1978年
虽然“垮掉的一代”一词最准确地指金斯堡及其密友(科尔索、奥洛夫斯基、凯鲁亚克、巴勒斯等),但“垮掉的一代”一词也与金斯堡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结识并结交的许多其他诗人联系在一起。这一术语的一个关键特征似乎是与金斯堡的友谊。与凯鲁亚克或巴勒斯的友谊或许也适用于此,但这两位作家后来都努力与“垮掉的一代”这个名称划清界限。他们对这一术语的不满部分源于将金斯堡误认为是其领袖。金斯堡从未声称自己是某个运动的领袖。他声称,这一时期与他结交的许多作家都拥有许多相同的意图和主题。这些朋友包括:大卫·阿姆拉姆、鲍勃·考夫曼;黛安·迪·普里玛;吉姆·科恩;与黑山学院相关的诗人,例如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克里利和丹尼斯·莱弗托夫;与纽约学派相关的诗人,例如弗兰克·奥哈拉和肯尼斯·科赫。勒罗伊·琼斯,后来改名为阿米里·巴拉卡,他在读完《嚎叫》后,用一张卫生纸给金斯伯格写了一封信。巴拉卡的独立出版社图腾出版社出版了金斯伯格的早期作品。[61][需要补充引文]在巴拉卡组织的一次聚会上,金斯伯格结识了兰斯顿·休斯,当时奥内特·科尔曼正在演奏萨克斯管。[62]
与鲍勃·迪伦(犹太人)的肖像,摄于1975年
金斯伯格晚年在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与蒂莫西·利里、肯·克西、亨特·S·汤普森和鲍勃·迪伦等人成为朋友。金斯伯格去世前几个月,在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街区的一家书店“书匠”(Booksmith)举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朗读。[63] 1993年,金斯伯格访问了缅因大学奥罗诺分校,向90岁的卡尔·拉科西致敬。
佛教与奎师那( Krishna)
另见:A. C. 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和咒石舞
1950年,凯鲁亚克开始学习佛教[65],并与金斯伯格分享了他从德怀特·戈达德的佛教圣经中学到的知识。[65] 金斯伯格正是在那时第一次听说了四圣谛和《金刚经》等经典。金斯伯格的支持帮助奎师那运动在纽约的波西米亚文化中建立起来。
金斯伯格的精神之旅始于早期自发的幻觉,并延续到早年与加里·斯奈德的印度之旅。[65] 斯奈德曾在京都大德寺第一禅学院学习。斯奈德一度吟诵般若波罗蜜多经,用金斯伯格的话来说,“这让我大开眼界”。金斯伯格对此产生了兴趣,前往隆德寺拜见达赖喇嘛和噶玛巴。金斯伯格继续他的旅程,在噶伦堡遇见了敦珠仁波切,敦珠仁波切教导他:“如果你看到可怕的事物,不要执着它;如果你看到美好的事物,也不要执着它。”
回到美国后,他在纽约市的一条街头偶然遇到了秋阳创巴仁波切(两人试图搭乘同一辆出租车),[67] 秋阳创巴仁波切是一位噶举派和宁玛派的藏传佛教大师,这促使他成为了秋阳创巴仁波切的挚友和终身导师。[65] 金斯伯格帮助创巴仁波切和纽约诗人安妮·沃尔德曼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那洛巴大学创办了杰克·凯鲁亚克无形诗学学院。
金斯伯格也参与了克里希纳教。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将念诵哈瑞·奎师那真言融入到他的宗教实践中。在得知西方世界哈瑞奎师那运动的创始人A. C. 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在纽约租了一家店面后,他与帕布帕德结为好友,经常拜访他,并推荐出版商出版他的书籍,一段富有成果的友谊由此开启。萨茨瓦鲁帕·达萨·哥斯瓦米在其传记《圣帕布帕德·利拉姆塔》中记录了这段关系。金斯伯格捐赠了金钱、物资和自己的名誉,帮助这位斯瓦米建立了第一座神庙,并陪同他四处巡回宣传他的事业。
艾伦·金斯伯格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迎接A. C. 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 1967年1月17日
尽管金斯伯格不同意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的许多禁令,但他经常公开吟唱哈瑞·奎师那真言,将其作为自己哲学的一部分[69],并宣称这能带来一种狂喜的状态。[70] 他很高兴看到来自印度的正宗斯瓦米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正试图在美国传播这种唱诵。金斯伯格与蒂莫西·利里、加里·斯奈德和艾伦·沃茨等反主流文化思想家一起,希望将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和他的唱诵融入嬉皮士运动,并同意参加“真言摇滚舞会”,将这位斯瓦米介绍给海特-阿什伯里的嬉皮士社区。
1967年1月17日,金斯伯格协助策划并组织了在旧金山国际剧院为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举办的招待会。
音乐和吟诵都是金斯伯格诗歌朗诵时现场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76] 他经常用簧风琴自奏,也常有吉他手伴奏。据信,印度佛教诗人纳加尔俊(Nagarjun)在贝拿勒斯向金斯伯格介绍了簧风琴。据马莱·罗伊·乔杜里(Malay Roy Choudhury)称,金斯伯格在向亲戚学习时,包括向他的表妹萨维特里·班纳吉(Savitri Banerjee)学习,从而完善了自己的演奏技巧。[77] 1968年9月3日,金斯伯格在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主持的电视节目《火线》(Firing Line)中询问他是否能唱一首赞美克里希纳神的歌,巴克利同意了,诗人一边用簧风琴悲伤地演奏,一边缓缓吟诵。据巴克利的同事理查德·布鲁克希瑟 (Richard Brookhiser) 称,主持人评论说这是“我听过的最轻松自然的克里希纳 (Krishna) 的歌”。[78]
在1967年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的人类聚会 (Human Be-In)、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1970年耶鲁大学校园举行的黑豹党集会上,艾伦都通过音响系统连续数小时反复吟唱“唵”。[79]
金斯伯格在歌曲《贫民窟被告》(Ghetto Defendant) 中吟诵《心经》,进一步将咒语带入摇滚乐的世界。这首歌收录于英国第一波朋克乐队 The Clash 1982年的专辑《战斗摇滚》(Combat Rock) 中。
Mantra-Rock Dance 宣传海报以艾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和主要摇滚乐队为特色。
金斯伯格与孟加拉的饥饿主义诗人取得了联系,尤其是马来人罗伊·乔杜里 (Roy Choudhury),后者向金斯伯格介绍了印度皇帝贾拉勒丁·穆罕默德·阿克巴 (Jalaluddin Mohammad Akbar) 的“三头鱼”。三条鱼象征着所有思想、哲学和宗教的共存。[80]
尽管金斯伯格对东方宗教颇有好感,但记者简·克莱默认为,他和惠特曼一样,信奉一种“美国式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植根于人文主义,以及浪漫而富有远见的人类和谐理想”。[81]
艾伦·金斯伯格遗产管理委员会与宝石之心国际组织于2021年在纽约市美国西藏之家合作举办了“转变思想:至尊格勒仁波切与友人”展览,这是一个画廊和在线展览,展出了艾伦·金斯伯格的学生格勒仁波切的照片。金斯伯格与格勒仁波切有着“不解之缘”。[82][83] 金斯伯格在斯坦福大学的照片档案中展出了50张底片,以颂扬“艾伦和仁波切之间的独特关系”。展览精选了包括达赖喇嘛、藏学家和学生在内的众多西藏大师,这些从未公开过的照片“都参考了艾伦在接触印版和他圈出准备印刷的照片上所做的大量笔记”。[84]
疾病与逝世
1960年,他因热带疾病接受治疗,据推测,他因医生注射的未消毒针头感染了肝炎,这导致了他37年后的死亡。[85]
金斯伯格一生吸烟,尽管他曾因健康和宗教原因尝试戒烟,但晚年繁忙的日程安排让他难以戒烟,最终他又开始吸烟。
20世纪70年代,金斯伯格两次轻微中风,最初被诊断为贝尔氏麻痹症,导致他严重瘫痪,一侧面部肌肉出现类似中风的下垂。晚年,他还经常患高血压等小病。这些症状很多都与压力有关,但他从未放慢脚步。
艾伦·金斯堡,1979年
金斯堡凭借《美国的陨落》(与艾德里安·里奇合著的《潜入沉船》)荣获197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1986年,金斯堡在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荣获金花环奖,他是继W. H.奥登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美国诗人。在斯特鲁加,金斯堡会见了其他金花环奖得主布拉特·奥库贾瓦和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
1989年,金斯堡出演了罗莎·冯·普劳恩海姆执导的获奖影片《沉默=死亡》,该片讲述了纽约市同性恋艺术家为争取艾滋病教育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权利而进行的抗争。[87]
1993年,法国文化部长授予金斯伯格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金斯伯格继续尽力帮助他的朋友:他自掏腰包给赫伯特·亨克(Herbert Huncke)捐款,定期给邻居亚瑟·罗素(Arthur Russell)提供延长线,供他家用录音设备供电[88][89],并娶了身无分文、吸毒成瘾的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
除了1997年2月20日在纽约大学诗歌朗诵会上作为特别嘉宾亮相外,金斯伯格于1996年12月16日在旧金山的“书匠书店”(The Booksmith)举行了被认为是他最后一次的朗诵会。
金斯伯格因充血性心力衰竭住院治疗,但未获成功。最后一次出院回家后,他继续打电话与通讯录里的几乎所有人告别。有些电话里充满了悲伤,甚至被哭声打断,而另一些电话里则充满了喜悦和乐观。[90]金斯伯格在病危期间继续写作,他的最后一首诗《我不会做的事(怀旧)》写于3月30日。
1997年4月5日,他在曼哈顿东村的阁楼中逝世,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终年70岁,因肝炎并发症罹患肝癌去世。[19] 格雷戈里·科索、罗伊·利希滕斯坦、帕蒂·史密斯等人纷纷前来吊唁。[92] 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安葬在纽瓦克戈梅利·切塞德公墓的家族墓地中。[93] 奥洛夫斯基为他默哀。
1998年5月14日,圣约翰大教堂举行了一场悼念活动,约2500名金斯伯格的朋友和粉丝出席。[94][95][96]
1998年8月,包括卡特菲什·麦克达里斯在内的多位作家在金斯伯格的农场举行了一场集会,以纪念艾伦和“垮掉的一代”。[97]
《心灵捕手》(1997年12月上映)是献给金斯伯格和四个月后去世的巴勒斯的。[98]
社会和政治活动
言论自由
金斯伯格乐于谈论禁忌话题,这使他在保守的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没有一家信誉良好的出版社会考虑出版《嚎叫》。当时,《嚎叫》中使用的这种“性话题”被一些人认为是粗俗的,甚至是色情的,可能会被依法起诉。[45] 金斯伯格在诗中使用了诸如“口交者”、“被干屁股”和“屄”等词语来描绘美国文化的不同方面。当时,许多讨论性的书籍都被禁,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45]金斯伯格所描述的性并非异性恋已婚夫妇之间的性行为,甚至并非长期恋人之间的性行为。相反,金斯伯格描绘的是随意的性行为。[45] 例如,在《嚎叫》中,金斯伯格赞扬了一位“让百万少女心动不已”的男人。金斯伯格使用了粗犷的描述和露骨的性语言,指出这位男人“饥肠辘辘、孤独地在休斯顿闲逛,寻找爵士乐、性爱或汤”。金斯伯格还在诗歌中探讨了当时禁忌的同性恋话题。《嚎叫》中充斥的露骨性语言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审判。金斯伯格的出版商因出版色情作品而被起诉,最终法官以这首诗具有“救赎的社会意义”为由,公开驳回了指控[99],从而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先例。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金斯伯格继续探讨争议性话题。从1970年到1996年,金斯伯格长期与美国笔会中心合作,致力于捍卫言论自由。在解释他如何处理争议性话题时,他经常提到赫伯特·亨克:他说,20世纪40年代,当他第一次认识亨克时,金斯伯格发现亨克因海洛因成瘾而病入膏肓,但当时海洛因是一个禁忌话题,亨克无处求助。[100]
在越南战争抗议活动中的作用
在197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抗议
金斯伯格是反战宣言《抵制非法权威的呼吁》的签署人之一,该宣言由激进知识分子团体“抵抗”的成员于1967年在反征兵者中传播。其他签名者和“抵抗”组织成员包括米切尔·古德曼、亨利·布劳恩、丹尼斯·莱弗托夫、诺姆·乔姆斯基、威廉·斯隆·科芬、德怀特·麦克唐纳、罗伯特·洛厄尔和诺曼·梅勒。[101][102] 1968年,金斯伯格签署了“作家和编辑战争税抗议”誓言,誓言拒绝纳税以抗议越南战争。[103] 后来,他成为“战争税抵抗”项目的发起人,该项目实践并倡导将税收抵抗作为一种反战抗议的形式。[104]
他亲临汤普金斯广场公园骚乱当晚(1988年),并向《纽约时报》提供了目击证词。[105]
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在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肆虐的年代,金斯伯格公开谈论他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以及他对昔日共产主义英雄和劳工运动的钦佩。我钦佩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许多其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物。[106][107]金斯伯格是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的成员。[108]在《美国》(1956年)一书中,金斯伯格写道:“美国,我小时候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我并不后悔。” 传记作家乔纳·拉斯金声称,尽管金斯伯格经常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正统观念,但他持有“自己独特的共产主义观点”。政府或任何暴力政府……我必须说,我所观察到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武装政府与暴力政府之间几乎没有区别”。[110]
金斯伯格曾前往多个共产主义国家推广言论自由。他声称,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欢迎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当他们将他视为麻烦制造者时,往往会转而反对他。例如,1965年,金斯伯格因公开抗议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而被古巴驱逐出境。[111] 古巴人将他送往捷克斯洛伐克。在被命名为“五月之王”(Král majálesu,[112] 一个学生节日,庆祝春天和学生生活)一周后,金斯伯格因涉嫌吸毒和公共场合醉酒而被捕,安全机构StB没收了他的几件作品,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淫秽且道德败坏。金斯伯格随后于5月7日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 1965年,[111][113] 受德国国家安全局(StB)命令。[114] 瓦茨拉夫·哈维尔指出,金斯伯格是他重要的灵感来源。[115]
同性恋权利
金斯伯格最重要且最具争议的贡献之一是他对同性恋的公开态度。金斯伯格是同性恋自由的早期倡导者。1943年,他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堆积如山的同性恋倾向”。他在诗歌中公开而生动地表达了这种渴望。[116] 他还在其《名人录》中将终身伴侣彼得·奥洛夫斯基列为配偶,以此为同性婚姻的标志。后来的同性恋作家将他对同性恋的坦诚讨论视为一个开端,让他们可以更公开、更诚实地谈论一些以前常常只是暗示或用比喻来提及的事情。[100]
通过对性进行生动细致的描写,以及频繁使用被视为不雅的语言,他挑战了——并最终改变了——淫秽法。[引文] [需要引用] 他坚定地支持那些挑战淫秽法的言论人士(例如威廉·S·巴勒斯和伦尼·布鲁斯)。
北美男童恋童癖协会 (NAMBLA) 会员
金斯伯格是北美男童恋童癖协会 (NAMBLA) 的支持者和会员,该协会是美国一个恋童癖和恋童癖倡导组织,致力于废除法定同意年龄法,并使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性关系合法化。[117][需要引用] 金斯伯格表示,他加入该组织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118] 他表示:“对 NAMBLA 的攻击散发着政治恶臭、为利益而进行的迫害、缺乏幽默感、虚荣、愤怒和无知……我加入 NAMBLA 是因为我也爱男孩——每个有点人性的人都爱男孩。”[119] 1994 年,金斯伯格出演了一部关于 NAMBLA 的纪录片,名为《鸡鹰:爱男孩的男人》(播放于 NAMBLA 网站)。艾伦在一次演讲中朗读了一首“献给青春的生动颂歌”(他用男同性恋俚语“chickenhawk”来表达)。[117] 他朗读了一首诗《甜心男孩,给我你的屁股》(Sweet Boy, Gimme Yr Ass),出自他所著的《心灵呼吸》(Mind Breaths)[120]。这本诗集被他称为“恋童癖狂想曲”,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与男孩发生性关系的场景。[121]
安德里亚·德沃金在她2002年出版的《心碎》(Heartbreak)一书中声称,金斯伯格与北美男童恋协会(NAMBLA)结盟别有用心:
1982年,各大报纸以大标题报道最高法院裁定儿童色情制品非法。我当时非常激动。我知道艾伦不会激动。我当时确实以为他是个公民自由主义者。但事实上,他是个恋童癖者。他加入北美男童恋协会并非出于某种疯狂而抽象的信念,认为该协会的声音必须被听到。我是认真的。以下是艾伦直接对我说的话:并非源于我的推断。他对自己与儿童发生性关系的权利极其强硬,并且不断追求未成年男孩。[122]
金斯伯格在谈及他曾经的好友德沃金时说道[123]:
我从安德里亚学生时代就认识她了。有一次我跟她说,我年轻时有过很多婚外情,对象都是16、17、18岁的人。我说:“你打算怎么办?把我送进监狱吗?” 她说:“你应该枪毙你。” 问题是,她年轻时遭受过性骚扰,至今仍未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现在她把这种情绪发泄在普通的恋人身上。[124]
娱乐性毒品
艾伦·金斯伯格、蒂莫西·利里和约翰·C·利利,摄于1991年
金斯伯格经常谈论吸毒问题。他组织了“大麻合法化运动”(LeMar)的纽约市分会。[125]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积极致力于揭开LSD的神秘面纱,并与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共同致力于推广LSD的普及使用。数十年来,他一直倡导大麻合法化,同时在其著作《放下你的香烟》(Put Down Your Cigarette Rag,别吸烟)中警示读者警惕烟草的危害:“别吸烟,别吸烟,尼古丁,尼古丁,别吸烟 ...除了与麦考伊合作之外,金斯伯格还就此事亲自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对质,但赫尔姆斯否认中央情报局与贩卖非法毒品有任何关系。[127][129] 金斯伯格撰写了许多散文和文章,研究和收集中央情报局涉嫌参与贩毒的证据,但直到 1972 年麦考伊出版了他的书,人们才开始认真对待他。[127] 1978 年,金斯伯格收到《纽约时报》主编的一封信,为没有认真对待他的指控而道歉。[130] 他的歌曲/诗歌《CIA Dope calypso》探讨了政治话题。美国国务院回应麦考伊最初的指控,称他们“无法找到任何证据证实这些指控,更不用说确凿的证据了”。[131] 随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监察长[132]、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33]和美国参议院情报活动政府行动研究特别委员会(又称丘奇委员会[134])的调查也认定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作品
金斯伯格早期的诗歌大多采用押韵的正式格律,这与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偶像威廉·布莱克的风格相似。他对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的钦佩促使他更加认真地对待诗歌。1955年,在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建议下,金斯伯格退出了工作,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135]不久之后,他创作了《嚎叫》。这首诗使他和“垮掉的一代”的同辈们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并让他得以以职业诗人的身份度过余生。晚年,金斯伯格进入学术界,自1986年起直至去世,一直担任布鲁克林学院的杰出英语教授,教授诗歌。[136]
朋友的启发
金斯伯格一生都声称,他最大的灵感来自凯鲁亚克的“自发散文”概念。他认为文学应该发自灵魂,不受意识的限制。金斯伯格比凯鲁亚克更容易修改。例如,当凯鲁亚克看到《嚎叫》的初稿时,他很不喜欢金斯伯格用铅笔进行的编辑性修改(例如,在第一行中将“黑色”和“愤怒”调换位置)。凯鲁亚克只是在金斯伯格的坚持下才写下了他的自发散文概念,因为金斯伯格想学习如何将这种技巧运用到他的诗歌中。[22]
《嚎叫》的灵感源自金斯堡的朋友卡尔·所罗门,《嚎叫》正是献给他的。所罗门是一位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爱好者(他把金斯堡介绍给了阿尔托),他患有临床抑郁症。所罗门曾想自杀,但他认为符合达达主义的自杀方式是去精神病院要求进行脑白质切除术。精神病院拒绝了,并给他提供了多种治疗方案,包括电击疗法。《嚎叫》第一部分的最后部分很大程度上描述了这种情况。
他还强调,摩洛克在多个方面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决定反抗社会构建的控制系统——从而对抗摩洛克——是一种自我毁灭。金斯堡在《嚎叫》中提到的许多角色,例如尼尔·卡萨迪和赫伯特·亨克,都因滥用药物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而自我毁灭。《嚎叫》的个人层面或许与政治层面同样重要。卡尔·所罗门,一个因反抗社会而毁灭的“最优秀头脑”的典型例子,与金斯堡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息息相关:“终于和母亲做爱了”这句台词出现在关于卡尔·所罗门的长篇章节之后,而在第三部分中,金斯堡说道:“我和你一起在罗克兰,你模仿着我母亲的影子。”金斯堡后来承认,创作《嚎叫》的动力源于对病弱母亲的同情,而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他直接以1959年的《卡迪什》(Kaddish)[22]来探讨这个问题。该诗在天主教工人周五晚会上首次公开朗读,可能是因为与托马斯·默顿的联系。[138]
导师和偶像的启发
金斯伯格的诗歌深受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开创的美国现代主义风格)、浪漫主义(特别是威廉·布莱克和约翰·济慈)、爵士乐的节奏和韵律(特别是查理·帕克等波普音乐家的节奏)以及他自身的噶举派佛教修行和犹太背景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继承了英国诗人兼艺术家威廉·布莱克、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传承下来的富有远见的诗歌风格。金斯伯格诗歌的力量、探索性的专注力、悠长而轻快的诗行,以及新世界的活力,都与他所宣称的灵感源源不断相呼应。[22][100][115]
他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通信,后者当时正在创作关于他家附近工业城市的史诗《帕特森》。在参加了威廉姆斯的朗诵会后,金斯伯格寄给了这位老诗人几首诗,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这些早期诗歌大多押韵、有韵律,并使用了像“你”这样的古体代词。威廉姆斯不喜欢这些诗,并告诉金斯伯格:“在这种模式下,完美是基本的,而这些诗并不完美。”[22][100][115]
尽管威廉姆斯不喜欢这些早期诗歌,但他喜欢金斯伯格信中那种活力四射的风格。我已将这封信收录在《帕特森》的后半部分。他鼓励金斯伯格不要效仿古代大师,而是要用自己的声音和普通美国人的声音说话。从威廉姆斯那里,金斯伯格学会了专注于强烈的视觉形象,这与威廉姆斯自己的座右铭“唯有物,无所求”相符。学习威廉姆斯的风格,使他从早期的形式主义作品转向了松散、口语化的自由诗体。早期突破性的诗歌包括《砌砖工的午餐时间》和《梦境记录》。[22][115]
卡尔·所罗门向金斯伯格介绍了安东尼·阿尔托(《结束上帝的审判》和《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和让·热内(《花之圣母》)的作品。菲利普·拉曼蒂亚向他介绍了其他超现实主义者,超现实主义持续对他产生影响(例如,《卡迪什》的部分内容就受到了安德烈·布勒东《自由联盟》的启发)。金斯伯格声称,《嚎叫》和其他诗歌中重复的重复运用受到了克里斯托弗·斯马特在其诗歌《欢腾的一天》等作品中的启发。金斯伯格还声称自己受到了其他更传统的影响,例如:弗朗茨·卡夫卡、赫尔曼·梅尔维尔、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埃德加·爱伦·坡和艾米莉·狄金森。[22][100]
金斯伯格还对俳句和保罗·塞尚的绘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中汲取了一个对他的作品至关重要的概念,他称之为“眼球踢”。我在观看塞尚的画作时注意到,当眼睛从一种颜色移到另一种对比色时,眼睛会痉挛,或者说“踢”。同样,我发现,两种看似对立的事物之间的对比也是俳句的一个常见特征。金斯伯格在他的诗歌中运用了这种技巧,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弱者与强者,高雅文化的产物与低俗文化的产物,神圣与邪恶。金斯伯格最常用的例子是“氢气点唱机”(后来成为菲利普·格拉斯创作的一首循环歌曲的标题,歌词取自金斯伯格的诗歌)。另一个例子是金斯伯格在鲍勃·迪伦1966年紧张刺激的电吉他巡演中对迪伦的评价。迪伦在安非他命[139]、鸦片[140]、酒精[141]和迷幻药[142]的混合作用下,像个服用了右旋安非他命的小丑。“眼球踢”和“氢气点唱机”这两个短语都出现在《嚎叫》中,还有一句塞尚的原话:“永恒的上帝之父”。[100]
音乐的灵感
另见:《纯真与经验之歌》(艾伦·金斯堡专辑)
艾伦·金斯堡也从音乐中汲取灵感。他经常在诗歌中融入音乐,总是用一架古老的印度簧风琴创作旋律,并在朗诵时演奏。[143] 他为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创作并录制了伴奏音乐。他还录制了其他几张专辑。为了创作《嚎叫》和《威奇托漩涡经》,他与极简主义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合作。
金斯堡曾与鲍勃·迪伦、冲撞乐队、帕蒂·史密斯[144]、菲尔·奥克斯和富格斯乐队[51]等艺术家合作,从他们身上汲取灵感,并激励他们。他与迪伦合作过各种项目,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145]
1981年,金斯堡录制了一首名为《鸟脑》的歌曲。他由“胶子乐队”(The Gluons)伴奏,这首歌作为单曲发行。[146] 1996年,他与保罗·麦卡特尼和菲利普·格拉斯共同创作了歌曲《骷髅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keletons),[147] 这首歌在当年的Triple J Hottest 100单曲榜上排名第八。
风格与技巧
通过学习他的偶像和导师,以及从朋友那里获得灵感——更不用说他自己的实验——金斯伯格发展出了一种很容易被认定为金斯伯格式的个人风格。[148] 金斯伯格表示,惠特曼的长诗是一种动态技巧,很少有其他诗人敢于进一步发展,惠特曼也经常被拿来与金斯伯格比较,因为他们的诗歌都对男性体态进行了性感化处理。[22][100][115]
金斯伯格早期的许多长诗实验都包含某种形式的首语重复,即重复一个“固定基调”(例如《嚎叫》中的“谁”,《美国》中的“美国”),这已成为金斯伯格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149] 他后来表示,这只是一种依靠,因为他缺乏信心;他还不相信“自由飞翔”。[150] 20世纪60年代,在《卡迪什》的某些部分(例如“嘎嘎叫”)使用了首语重复之后,他基本上放弃了首语重复的形式。“后期节拍”鲍勃·迪伦以使用首语重复而闻名,例如在《纠结于蓝色》中,每节诗结尾都用这个短语代替了副歌。[100][115]
他早期对诗歌格式方法的几次实验,成为他后期诗歌风格的常规元素。在《嚎叫》的初稿中,每一行都采用了“阶梯式三行诗”的格式,让人联想到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151]。他在创作长诗时放弃了“阶梯式三行诗”,尽管阶梯式诗后来出现,尤其是在《美国的沦陷》的游记中。[需要引证] 可以说,他最重要的两首诗《嚎叫》和《卡迪什》都采用了倒金字塔的结构,大段大段地衔接小段。在《美国》中,他也尝试过长短诗的混合。[100][115]
金斯伯格成熟的风格运用了许多特定且高度发达的技巧,这些技巧体现在他在那洛巴教法中使用的“诗意口号”中。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未经编辑的心理联想,以揭示思维活动(“第一个想法,最好的想法。”“心灵是形状,思想是形状。”)。他更喜欢通过仔细观察的物理细节来表达,而不是抽象的陈述(“展示,不要讲述。”“除了事物之外,别无想法。”)[152] 在这些作品中,他继承并发展了现代主义写作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凯鲁亚克和惠特曼的作品中也有体现。
在《嚎叫》和其他诗歌中,金斯伯格从19世纪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史诗般的自由诗风格中汲取灵感。[153] 两人都热情洋溢地描写了美国民主的承诺(和背叛)、情色体验的核心重要性以及对日常生活真理的精神追求。《耶鲁评论》编辑J. D. 麦克拉奇称金斯伯格是“他那一代最著名的美国诗人,既是一股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文学现象。”麦克拉奇补充道,金斯伯格和惠特曼一样,“是一位老派的吟游诗人——气势恢宏,充满黑暗的预言,一部分是热情洋溢,一部分是祈祷,一部分是咆哮。他的作品最终是我们这个时代心灵的历史,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冲动。”麦克拉奇的讽刺悼词界定了金斯伯格(“一位垮掉的一代诗人,他的作品……通过将回收天才与慷慨的模仿同理心相结合而产生的新闻主义,以引起读者共鸣;总是充满抒情,有时甚至充满诗意”)和凯鲁亚克(“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垮掉的一代’中最耀眼的明星,他后来成为流行文化的象征……[尽管]实际上他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凯鲁亚克是一位独具匠心的天才,探索然后回答——就像一个世纪前的兰波一样,是出于必然而非选择——真实的自我表达的要求适用于美国唯一一位文学大师不断发展的灵动心灵……”)。
荣誉
他的诗集《美国的陨落》荣获197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类奖项。[14]
金斯伯格凭借《美国的陨落》(与艾德里安·里奇的《潜入沉船》合著)荣获197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14]
1979年,他荣获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金奖,并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15]
1986年,金斯伯格荣获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花环奖,成为继W. H. 奥登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美国诗人。在斯特鲁加,金斯伯格会见了其他金花环奖得主布拉特·奥库贾瓦和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
1989年,金斯伯格出演了罗莎·冯·普劳恩海姆执导的获奖影片《沉默=死亡》,该片讲述了纽约市同性恋艺术家为争取艾滋病教育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权利而展开的抗争。[87]
1993年,法国文化部长授予金斯伯格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95年,金斯伯格凭借其著作《大都会问候:1986-1992年的诗歌》入围普利策奖决赛。[16] 1993年,他被哥伦比亚出版社追授约翰·杰伊奖。[154][155]
2014年,金斯伯格成为“彩虹荣誉步行”的首批获奖者之一。“彩虹荣誉步行”是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区的一项星光大道,旨在表彰“在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LGBTQ人士。[156][157][158]
参考书目
《嚎叫及其他诗歌》(1956年),ISBN 978-0-87286-017-9
《卡迪什及其他诗歌》(1961年),ISBN 978-0-87286-019-3
《空镜:早期诗歌》(1961年),ISBN 978-0-87091-030-2
《现实三明治》(1963年),ISBN 978-0-87286-021-6
《雅格书信》(1963年)——与威廉·S·巴勒斯合著
《星球新闻》(1968年),ISBN 978-0-87286-020-9
《印度期刊》(1970年),ISBN 0-8021-3475-0
《早期布鲁斯:1971-1974年的拉格斯、民谣与簧风琴歌曲》(1975年),ISBN 0-916190-05-6
《愤怒之门:1948-1951年的押韵诗》(1972年),ISBN 978-0-912516-01-1
《美国的衰落:这些州的诗歌》(1973年),ISBN 978-0-87286-063-6
《铁马》(1973年)
艾伦·金斯堡的《逐字逐句:关于诗歌、政治与意识的讲座》(1974年),戈登·鲍尔编辑,ISBN 0-07-023285-7
《悲伤尘埃的荣耀:夏日林中工作时所作的诗》(1975)
《心灵呼吸》(1978),ISBN 978-0-87286-092-6
《冥王颂歌:1977-1980 年诗歌》(1981),ISBN 978-0-87286-125-1
《1947-1980 年诗集》(1984),ISBN 978-0-06-015341-0。 2006年,重新出版,并添加了后来的材料,名为《诗集1947-1997》,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白色裹尸布诗集:1980-1985》(1986年),ISBN 978-0-06-091429-5
《大都会问候诗集:1986-1993》(1994年)
《嚎叫注释》(1995年)
《光辉诗集》(1996年)
《诗选:1947-1995》(1996年)
《死亡与名望:1993-1997年的诗歌》(1999年)
《深思熟虑的散文:1952-1995》(2000年)
《嚎叫及其他诗歌》五十周年纪念版(2006年),ISBN 978-0-06-113745-7
《殉道与诡计之书:1937-1952 年的早期日记与诗歌》(达卡波出版社,2006 年)
《艾伦·金斯堡与加里·斯奈德书信选》(Counterpoint 出版社,2009 年)
《我在此致敬伟大的事业之初:劳伦斯·费林盖蒂与艾伦·金斯堡书信选,1955-1997 年》(城市之光出版社,2015 年)
《我这一代最优秀的思想:垮掉一代文学史》(格罗夫出版社,2017 年)
To Frank O’Hara
Sometimes when my eyes are red
I go up on top of the RCA Building
and gaze at my world, Manhattan—
my buildings, streets I’ve done feats in,
lofts, beds, coldwater flats
—on Fifth Ave below which I also bear in mind,
its ant cars, little yellow taxis, men
walking the size of specks of wool—
Panorama of the bridges, sunrise over Brooklyn machine,
sun go down over New Jersey where I was born
& Paterson where I played with ants—
my later loves on 15th Street,
my greater loves of Lower East Side,
my once fabulous amours in the Bronx
faraway—
paths crossing in these hidden streets,
my history summed up, my absences
and ecstasies in Harlem—
—sun shining down on all I own
in one eyeblink to the horizon
in my last eternity—
matter is water.
Sad,
I take the elevator and go
down, pondering,
and walk on the pavements staring into all man’s
plateglass, faces,
questioning after who loves,
and stop, bemused
in front of an automobile shopwindow
standing lost in calm thought,
traffic moving up & down 5th Avenue blocks behind me
waiting for a moment when ...
Time to go home & cook supper & listen to
the romantic war news on the radio
... all movement stops
& I walk in the timeless sadness of existence,
tenderness flowing thru the buildings,
my fingertips touching reality’s face,
my own face streaked with tears in the mirror
of some window—at dusk—
where I have no desire—
for bonbons—or to own the dresses or Japanese
lampshades of intellection—
Confused by the spectacle around me,
Man struggling up the street
with packages, newspapers,
ties, beautiful suits
toward his desire
Man, woman, streaming over the pavements
red lights clocking hurried watches &
movements at the curb—
And all these streets leading
so crosswise, honking, lengthily,
by avenues
stalked by high buildings or crusted into slums
thru such halting traffic
screaming cars and engines
so painfully to this
countryside, this graveyard
this stillness
on deathbed or mountain
once seen
never regained or desired
in the mind to come
where all Manhattan that I’ve seen must disappear.



/cloudfront-us-east-1.images.arcpublishing.com/pmn/6G73VQNI45DK7AJHO3TVN7AYA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