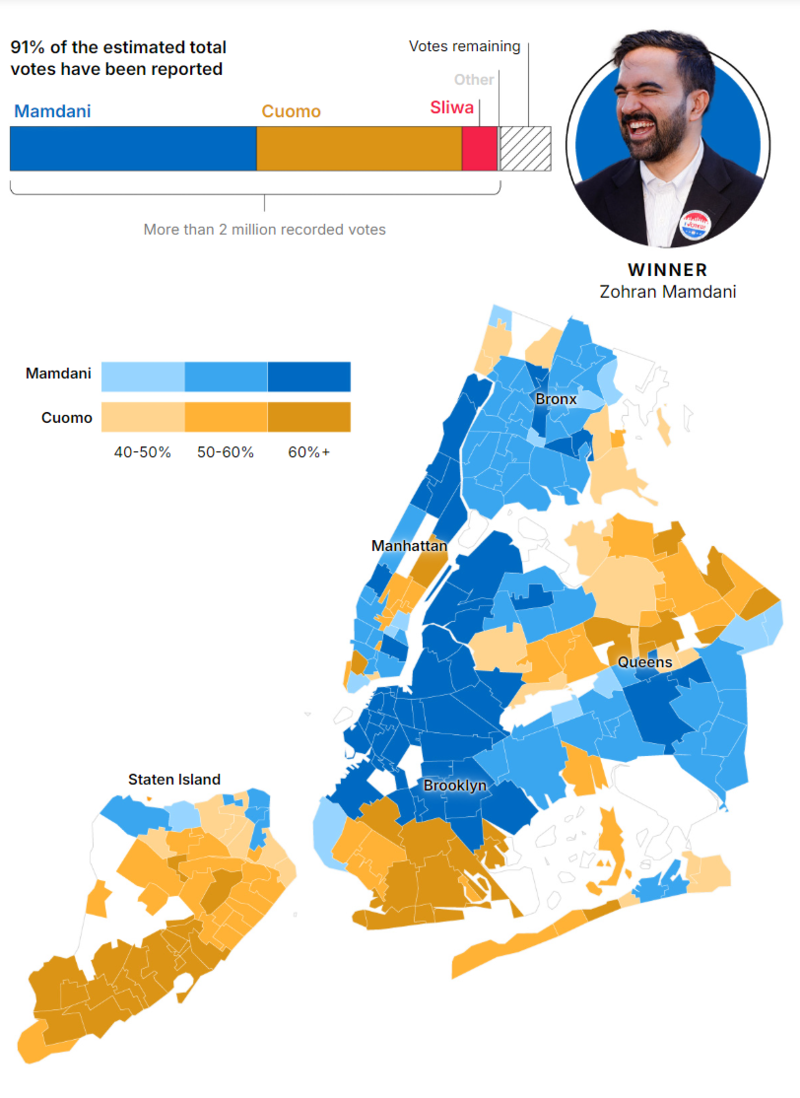《纽时》刊文:我们还有什么办法限制总统的权力?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戈德史密斯先生是乔治·W·布什政府下的前助理司法部长,与鲍勃·鲍尔(Bob Bauer)一起创办了一份关于总统与行政权力的通讯。
唐纳德·特朗普(专题)具有破坏性的第二任期已经揭示了总统职位的全部潜在权力。
他的政府最明显地展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全面消除行政部门内部的法律和规范性制衡,系统性地不尊重司法程序,滥用政府权力打压对手,以及使用具有破坏性的言论和恶意攻击。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特朗普先生扩大总统职权的许多努力实质上是建立在近期历届总统过度行为的基础上。
过去几十年总统行动的整体模式显示出权力攫取的不断升级,这使国家在特朗普再次上任前就已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总统职位需要改革,美国人必须考虑各种方法——无论在当今政治环境下这些方法看起来多么不切实际——来实现这一目标。
扩张主义的总统行为可以追溯至乔治·华盛顿,他因使用宪法中广泛但未定义的"行政权力"而招致君主制的指控。从那时起,总统职位凭借其松散的设计不断发展壮大,在内战和新政时期出现了重大飞跃。
这一趋势在20世纪继续,得益于大众传播的兴起、来自国会的实质性权力授权以及最高法院的支持。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激进总统作风,在未被充分认识的程度上,正按照他的现代前任所设计的剧本运作。
他利用紧急权力实施广泛关税的做法类似于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举动。他声称不可触及的国家安全权力的主张呼应了9·11袭击后乔治·W·布什政府(我曾在其中任职)提出的论点。
几十年来,总统一直将赦免作为政治或个人恩惠,或规避个人法律风险的手段。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将这种做法推向了新的极端,随后拜登总统也预先赦免了他的儿子和家人以及其政府和国会成员,遵循了类似模式。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已经发布了许多为自身服务的赦免令。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计划是奥巴马总统用于大规模且有时在法律上可疑的政策举措战略的继承者,包括一些(涉及移民(专题)的)奥巴马早先承认他缺乏采取行动权力的领域。拜登也承认缺乏权力,但随后单方面采取行动寻求免除学生贷款。
特朗普无视法定限制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和功绩制度保护委员会等独立机构的官员。但在2021年,拜登扩展了最高法院的单一行政案例法,解雇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保障局局长。2021年,法律作家马克·约瑟夫·斯特恩(Mark Joseph Stern)指出,拜登是"第一个单一行政者"。
拜登还清除了行政部门中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特朗普留任官员,包括艺术和荣誉机构成员、美国行政会议和国土安全部咨询委员会成员。拜登政府对这些解雇的辩护导致了司法先例,特朗普现在正在更大规模上利用这些先例来清理门户。
特朗普政府还在不执行联邦法律方面延续了过去总统的做法——例如让TikTok继续存在,尽管国会颁布了禁令。这种做法在奥巴马政府中找到了现代根源,该政府在涉及移民、大麻和奥巴马医改的高调案件中主张广泛的不执行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改变了这些法律的含义。
支出方面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正如最近一篇论文指出,"过去几位总统都采取了重大的单方面行动,侵犯了国会对联邦支出的控制。"特朗普2.0版本大大扩大了这种单边主义模式。
对教育机构的政府改造也是如此。奥巴马政府在法律上可疑的威胁要撤回大学的联邦资金,诱导其对性侵犯和骚扰规则进行重大改革。特朗普政府因反犹太主义和意识形态俘获而攻击大学,依赖于相同的潜在逻辑——尽管这些攻击更加强硬且在法律上更加可疑,在预判案件和冻结资金时没有遵循程序。
无论是否合理,起诉政治对手这一极具争议性的步骤是由拜登政府而非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虽然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联邦起诉在法律上是严肃的,但特朗普和支持者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州和地方层面更广泛的党派行动的一部分,利用法律系统阻止特朗普参加2024年竞选。
共和党人正确地抗议了许多民主党政府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现在成为特朗普所依赖的先例。他们还合理地抱怨情报界的政治化和武器化;政治利用国税局;行政部门对私人言论的威胁以及排除和取消敌对媒体的合法性;攻击联邦法院;以及过度使用紧急权力。
特朗普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做所有这些事情——通常得到那些曾经反对这些策略的人的掌声。
特朗普政府与历届政府的制度行为比较研究,以及共和党对行政权力立场的历时性分析,其学术价值既不在于揭露政治对手的自相矛盾(“gotcha”),也不在于通过指责对方以转移焦点(“whataboutism”)。这些比较实则构成了观测宪政体系中行政权力约束机制持续弱化过程的关键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约束力逐渐降低的系统性发展轨迹。
看似为短期收益而合理的传统限制的小偏离,成为未来升级的路线图。一个总统任期的新举措成为下一个总统稍微提高一点的先例。政治光谱两端都在不执政时反对这些升级,但当他们掌握总统权力时依赖它们进一步推进。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战略规划者与政策架构师已对前几届政府在行政权力扩张方面的制度创新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与深度借鉴。若无法打破这种历史性循环模式,我们有充分理由预期,未来的民主党执政团队将会延续并深化这些行政权力扩张实践——其中可能包括针对各类制衡性权力中心动用国家机器资源,这一政治策略的长期后果将使当前支持此类权力扩张的共和党人士深感懊悔。
反复升级的总统权力攫取对国家来说是可怕的。它们导致了越来越极端的总统政策,不同政府之间越来越大的政策摇摆,以及司法部越来越政治化和政府更广泛的武器化。
它们也损害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必须裁决越来越多和极端的总统权力主张,而且并不总是明智地解决这些案件,往往无法以政治上无争议的方式解决。
对总统职位施加实质性限制是有明确理由的。这种努力必须让我们回到的不是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前的时代,而是回到国会而不仅仅是总统在国内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以及法律和规范阻止总统短期内攫取一切的时代。
但我们如何达到那里坦率地说很难想象。
一条途径通过最高法院。其最近的一些原则创新——缩小对联邦机构的司法尊重并要求国会对行政政策的"重大问题"明确表态——旨在限制总统未经国会真正授权的行动。许多民主党人在拜登担任总统时谴责这些原则,但现在非常乐意援引它们。这里有一个教训。
特朗普在拨款、机构重组、驱逐出境和公务员制度方面积极主张行政权力,为法院提供了澄清和约束该权力的机会。当杜鲁门总统在朝鲜(专题)战争期间试图接管钢铁厂以及布什总统在9·11袭击后主张过多单方面战争权力时,法院就是这样做的。法院还必须重新思考其最近对单一行政的一些让步,鉴于特朗普已经展示了全面单一行政可能造成的损害。
一条更重要但更陡峭的途径通过国会。很难夸大负责任的国会的衰落是总统失控的原因。有许多好的改革方案可以重组国会和竞选融资,使立法机构在政策制定和监督中发挥更严肃的作用。
困难的部分——基本障碍——是让功能失调的国会采纳它们。即使在拜登时期——在特朗普充满滥用权力的第一任期之后,民主党控制国会——国会也未能改革总统职位。
然而,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曾经不可想象的根本改革时期。这发生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而1970年代后越战、后水门事件的对总统制的重要改革在发生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特朗普2.0之后的清算——或者在它引发的报复之后——可能类似于1970年代的时刻,提供约束总统制和恢复国会首要地位的机会。
但仅靠司法审查或普通法律改革都不足以抑制近几十年来总统制已经变成的样子。我们必须考虑宪法修正案的可能性,以定义和约束行政部门。
这里的门槛极高,任务微妙。宪法改革的主要可能性包括缩小失控的赦免权;允许国会阻止不当的行政行动而无需通过新法律(这是最高法院在1983年宣布无效的一种曾被接受的做法);以及限制司法部各种形式的政治化。
每种类型的总统改革,以及对总统的所有有意义的约束,最终取决于选举一位领导人,正如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帝国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中所写,他"在自己心中体现了制衡"。
这反过来取决于现在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位像1976年吉米·卡特那样以缓和总统权力为平台竞选的候选人;一个能够克服分歧选出这样一位领导人的选民;以及一位在任内贯彻执行的总统。
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lgoldsmith)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以及前助理司法部长。他与鲍勃·鲍尔共同撰写了《特朗普之后:重建总统制》和通讯《行政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