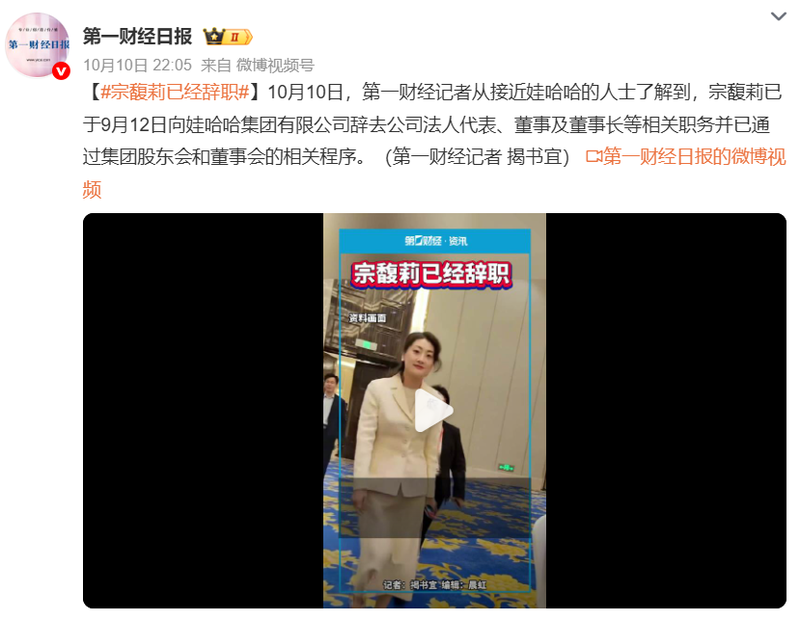百强县政府大院太“寒碜”,打了穷县大基建的脸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公众可以随意进出的县政府,才会让人觉得,那是“我们”的政府,是可以安心享受服务的地方。
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能接触到的最高政府层级,就是县政府。县政府机关发生的事情,最容易引起普通公众的高度关注。
近日,浙江象山县“寒碜”的政府大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照片中,象山县政府的大门显得简陋狭小,与现今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该县宣传部一工作人员表示,门面虽旧,但房屋一直能用,也没有漏水等问题,可以满足正常的办公标准,院内还有一个省级保护文物“淳熙井”。
公开资料显示,象山县曾在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中,位居全国第53位,成功入选“2024年中小城市优秀案例”。
01
有关县政府的消息,最近还有几则:
3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2年,湖南汉寿县实施“靓城战略”,“拆围透绿”工作,自2022年以来,汉寿县共拆除115处围墙、复绿9万多平方米。打通连片老旧小区,增设休闲广场、停车场。除中小学校外,县城38个机关和事业单位均拆除了围墙。
报道还称,早在2014年,湖北黄石市发出公告,自当年5月1日起,市级机关大院对市民开放,4月至9月为每天6:00至22:00;10月至次年3月为每天6:30至21:30。开放地点为除市级机关大院内办公大楼外的公共场所。
2016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各地积极响应。当年,安徽泾县10家政府机关大院自拆围墙,政府机关大院变成市民的社区公园,并通过增补绿化面积、道路及基础设施完善等项目改造,让市民享受更多绿色资源。此后,河南信阳市、安徽舒城县、绩溪县也开放了政府大院。其中,舒城县不仅开放了政府大院,还将院内公共卫生间、停车场和机关食堂向群众开放。
此外,部分政府大院虽设有院墙和大门,但始终对市民完全开放。在西藏察隅县政府大门几乎全年敞开。有一次不知谁家的羊群跑进来,啃光了一大片叶子。
4月26日《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土坯房县委大院为何受关注”提到,河南卢氏县的县委大院带有20世纪50年代的典型风格,西四东五九排“红砖”矮房、一座两层半砖楼疏朗有序排列其间。常年在这里办公的有200多名干部职工,还有包括县委常委等班子领导。
▲卢氏县的县委大院(澎湃新闻记者 李文姬/摄)
1986年春,在卢氏县委土坯房前院老县衙旧址出土了名为“圣谕碑”的古碑,碑上刻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字。当地人介绍,“圣谕碑”影响了卢氏历代为官者,有明代卢氏县令还一度将县衙更名为“亲民堂”。
4月29日,微信公众号“衢州发布”推送了市政府食堂对外开放的消息,公布的菜单里包含自选套餐,每份18元。同样,今年“五一”期间,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推出了20道“荣昌味道”小碗菜,价格从3元至18元不等。5月2日中午,一顿午饭时间,食堂就有8000名游客蜂拥而至,蒸了半吨米饭不够吃。
▲“五一”假期期间,衢州政府食堂对外开放(图/视频截图)
乡镇政府的食堂也在开门迎客。安徽黟县宏村镇春节期间,曾开放食堂接待游客,“五一”假期再度开放,每天菜品不重样;北京市门头沟区三个镇——清水镇、雁翅镇、斋堂镇也同步开放了政府共享食堂。这些食堂大多靠近景区,步行数分钟,或20分钟内车程可达,解决了游客辛苦和“吃饭难”问题。
02
今天中国内地一些县政府的上述举动,在王朝时期的县衙里不可想象。这从县衙的建筑结构就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大堂,具体的大堂各有名称。比如明朝时宛平县的大堂叫节爱堂,清朝时上海县的大堂叫清节堂,大堂有个一致性的别号——讼堂。所谓老爷升堂,听讼断案,场面都摆在这个大堂上。
大堂的背后是堂帐,犹如现在舞台上挂的“天幕”,幕布后面并非实实在在的墙壁,而是六扇门,又叫中门,专供县太爷升堂时进出,所以这堂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从中间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挂两边。
由中门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块石台,台上再放一张长方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这就是县太爷高高在上的地方了。
公案之上及两边,有印包、签筒、笔架、砚台和醒木,以及写有“回避”“肃静”等字样的虎头牌面之类。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楼的作用不同,它是用来作“放衙”的。所谓“放衙”,就是宣布县太爷下班。明清时期,衙门上班退堂的信号改为敲榔子击云板,但是堂鼓依旧放在那儿,专供来不及写帖子告状的老百姓鸣击叫冤用。
▲《九品芝麻官》剧照(图/视频截图)
大堂后是二堂,和大堂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公开审理,一个是秘密审理。二堂的后面,有的还安排有三堂,有的安排为后衙,也叫知县廨,包括县太爷的书房及其家属生活起居的上房、仆人房、师爷房、花厅等许多建筑。
其中最心脏部分的是签押房,是衙门一把手的办公厅。签押房,也就是机要办公室,上司下发或平行街署平移的机密文件,按规定也必须在签押房里拆阅。
古人往往称州县官署的具体办公场所为“堂前”或“门上”,这就是泛指大堂前面左右两侧的廊房式建筑了。从宋徽宗崇宁年间起,开封和祥符两县分知县属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大观年间,令天下州县都照此式修造,从此一直沿袭下来,统称“六房”。
五脏俱全的衙门以知县廨为中心。知县以下,还有丞、尉、主簿、典史等其他佐官和属员。按秦汉以来的传统,他们并不与县太爷合署办公,而是另有专门的署。这些署可以是放在县衙门内部或连在一起又单独对外开门的,也可以是靠近县衙门但单独建造的。不过有一点定为制度,即主管教育的学署必定单独起屋,以为如此才能显得更“清要”一点。(以上内容来自完颜绍元《天下衙门》)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古代衙门没什么公共性可言,它的功能和事务主要有三:第一,征收赋税及安排徭役;第二,治安和决断民事刑事纠纷;第三,掌管文教。个别时期可能会举办一些社会福利。它就是朝廷派驻地方的统治机构,并不为地方老百姓提供服务。
而且可以看出,在古代,闲杂人等不可以随意进出衙门。普通人只要不涉及上述三项衙门事物,通常也没什么事情要去衙门办理,都是自行解决,不必劳动官府。而因为交通不便,县令本人下乡很麻烦。朱元璋甚至规定,县令不准下乡,以免滋扰百姓。官民之间的直接互动,并不多见。
但这种衙门建筑显然不适合现代社会。现代政府有很多新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广义的经济功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财税收支、资产管理等等,不是几个人忙得过来的;古人的生、老、病、养、死,基本上自己解决,不跟政府有关,现在也要全部管起来了,要有相应的部门提供服务;过去的官学顶多只有一所,现在遍地是学校,政府也要负责;至于现在的治安及民事刑事,也远非古代可比。古代的衙门建筑,根本承载不了如此多的功能。
现代政府职能与古代政府相比,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本质上完全是两回事。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与县乡两级政府之间,可以说关系异常之多。县政府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公共建筑,而不再是古代的“统治机关”。
03
由于县令没有发展经济的考核指标,更没有“县财政”的概念之类,只要能将就使用,上级就不会给一笔修衙门的钱。加上县令的任期很短,一般只有三四年,所以,他们对县衙门的修造并不热心,得过且过,所谓“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是也,都是过客,修好也是别人享受,何必费这个神?
县令也是“理性经济人”,真要搞修建,还不如修水利,说不定可以在御史那里留个好名声,得到升迁机会。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有人看到修造政府办公场所的发财机会,有人在修造县政府时,获得权力膨胀的心理满足。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县级政府的办公大楼巍峨壮观,显得比五角大楼还气派,让人望而却步;有的门楼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让层级更高的政府机关黯淡失色。
这是在传统和现代面前的双重失序,一方面,它试图以现代方式,传承老百姓对县衙门的畏惧,另一方面,它又罔顾传统的“官不修衙”,利用“县财政”的自主性,挥洒自如,把县政府的修造变为满足私欲的举动。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县政府办公场所既丢失了传统衙门的“朴素”传统,也不具备现代政府办公场所的公共性。人们一方面以“朴素”的县衙门来批评县政府办公场所的奢华,另一方面,又以现代政府职能的“人民性”,批评其拒人于千里之外。
▲“五一”期间的荣昌区政府(图/CFP)
上文提及的多个地方县级政府则走出了上述窠臼,以朴素门面、开门接纳市民停车与休闲、开放机关食堂,向公众展示其“人民性”的一面,宣示其办公场所是公共建筑,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
对一个门禁森严,让人望而却步的县政府,一般公众不会觉得那个地方能够为“我”提供服务;公众可以随意进出的县政府,才会让人觉得,那是“我们”的政府,是可以安心享受服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