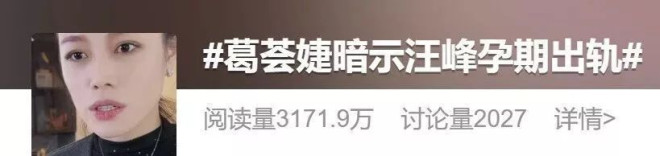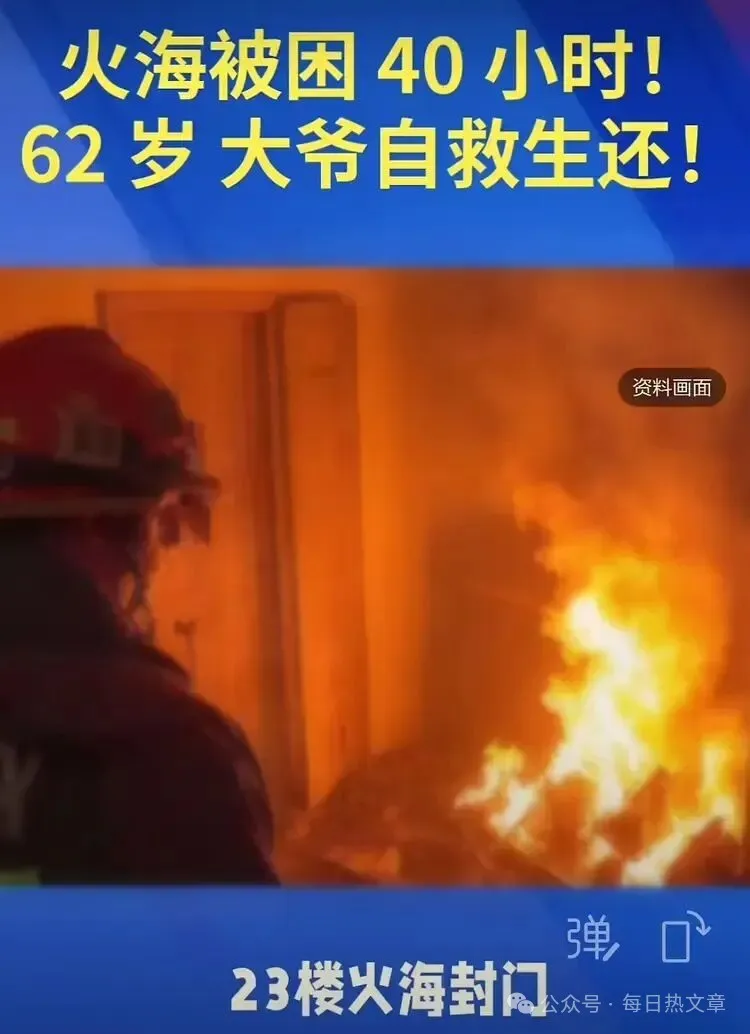当母亲询问网友,能否切除女儿的子宫....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在一堂性教育课上,老师苏艳雯问一个孩子,如果我用某某东西交换,让你脱裤子可以吗?孩子拒绝了。苏艳雯又问,那用糖果交换呢?孩子立刻起身要脱裤子。
苏艳雯没想到糖果的诱惑力那么强,她和同事不敢再在课堂上提“脱裤子”。她改问学生,如果我用糖果交换,摸一下你好不好?一个孩子没说话,起身,转过去,撅起屁股。
“我们跟家长讲,不要用条件交换的方式教育孩子,因为坏人也会跟孩子交换条件。”说这些时,苏艳雯坐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附近的咖啡店里。她短头发,戴眼镜,穿着蓝色短袖,面前放着一台合起来的笔记本电脑。苏艳雯是广州少年宫的性教育专家讲师,学生是心智障碍孩子,包括孤独症、唐氏综合征、罕见病等,这几年还来了不少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
2010年,苏艳雯在大学毕业后从事心智障碍性教育,今年是第15年。15年里,她陪伴心智障碍小孩,也陪伴家长——大部分心智障碍小孩遇到性问题时家长的反应是“紧张无措”,以至于孩子正常的需求被一再忽视、压抑甚至阻拦。比如自慰,心智障碍者很难想出瞒过父母的方式,他们一辈子活在家长眼皮下。在一些家庭,只要孩子一个人在房间里待得有点久,家长就会故意敲门,让孩子走出房间。
苏艳雯的工作是帮助孩子和家人正视他们的性与爱需求。
许多心智障碍孩子难以界定公共空间和隐私空间,也难以区分“表达喜欢”和“性骚扰”。当他们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心仪对象,可能会对他/她一直笑,或者尾随——可能被误认为“色狼”“故意骚扰”。苏艳雯会通过反复训练,帮他们区分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和交往边界。
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但心智障碍孩子一定要“确定”。他们会机械记忆规则,却难以灵活应用于现实生活。比如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孩,每次来教室都向苏艳雯热情问好,有一天课后,苏艳雯看到他在马路对面,向他挥手,男孩“像看到鬼一样”跑掉了——没人教过他在大街上看到老师要怎么回应。
显然,只依靠机械记忆和刻板行为很难“谈甜甜的恋爱”。苏艳雯的教学中也包含让孩子学会拒绝、接纳拒绝。
苏艳雯希望性教育课程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减少他们在公共场域中不恰当行为的可能(比如脱裤子、自慰),以及当发生相关问题时,他们能做什么(比如寻找洗手间等隐私场所,求助于家长)。因此,比起一般孩子性教育课程更偏向理论(讲生理变化的原理),心智障碍孩子性教育课程更偏向实践:学习基本技能。
比如月经课程,一般学校会教女性身体结构,月经周期的原理和健康的应对心态,但心智障碍的课堂上主要教一件事:如何使用卫生巾。
孤独症教育工作者吴良生曾参与训练一位孤独症女孩学习使用卫生巾。尽管做了大量前期训练,女孩依然不知道要主动使用,也不知道该何时更换。甚至在更换卫生巾5分钟后,就把它撕下来,拿在手里玩。
去年,一位母亲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她描述女儿是重度孤独症,完全不能自理。女孩来月经后,弄得手上、床上、衣服、家具上都是。这位母亲只能让女儿全天穿安睡裤,也许因为不舒服,女孩不停地用手抓私处,指甲缝里的血用软刷子都刷不干净。这位母亲询问网友,能否切除女儿的子宫。
自闭症癫痫孩子的母亲、博主马女士在今年3月写道,一位女性朋友、也是一位母亲,建议她带女儿做绝育手术,甚至摘除子宫。理由是,担心女孩长大后遭受性侵而怀孕。
课堂上,苏艳雯会带领孩子们通过情景模拟反复练习。她首先展示卫生巾,请他们触摸质感,一步步演示如何拆封,如何使用,如何把用过的卫生巾包起来,丢进垃圾桶,以及如果弄脏了裤子怎么办,还有很重要的,不要害怕经血。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好几个月和大量的耐心。还有的孩子无法教会,家长只能到点去学校帮孩子换卫生巾。
成长时期已经如此艰难,那么长大后呢?《大西洋月刊》曾报道那些成年的孤独症人士,发现他们会经历世界性难题“福利断崖”:成年后,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资助、同理心和关注将断崖式锐减,因为人们更关心的永远是下一个特殊孩子。正如美国自闭症研究者Paul Shattuck所说:“好像我们从未真正考虑过所有这些孩子最终会长大的事实。”苏艳雯说,除了社会支持部分的消失,家长们也可能在漫长的蹉跎中耗光了金钱和精气神,甚至,再也没有能量带他们走出家门。
以下是苏艳雯对凤凰网的讲述:
上周,我听一个家长说,深圳有两位孤独症人士结婚了,还摆了喜酒。家长们在群里面分享这个消息。我觉得很开心。很多人不认为心智障碍人士有结婚的需要和权利,人们更愿意把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放得更靠前,忽略他们真正的情感需求。
关于心智障碍孩子的婚恋问题,家长的态度是两极。有的家长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尊重孩子的需求。有的家长明确反对,他们照顾自己的孩子已经耗尽心力了。如果是两个特殊孩子结合,家长不清楚是否有能量照顾两个人,还担心孩子生的小孩也是特殊孩子。还有女孩家长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宝贝,虽然她承担不了太多的家庭责任,但嫁出去可能会受苦受累,所以不愿意。
有的是孩子有想法,家长不敢有想法。我问过一个21岁的孩子,你想过结婚吗?他说想过,但是爸爸说40岁以后才能结婚。意思是让孩子别想了。
我们班孩子也表达过“我想结婚”。我们第一节课会设置一些问题,在黑板两端分别贴上“同意”、“不同意”,让孩子们选择。我们会问“你喜欢吃榴莲吗”这类生活问题,也会问“你想结交朋友吗”“你想结婚吗”“想生孩子吗”。有孩子选择“同意”,有的“不同意”。
有一个女孩选择了想结婚。我们问她为什么,她就说,我要穿婚纱,要穿漂亮的蓬蓬裙。但是她选择不生小孩,她觉得小孩很烦。曾经有一个孩子说,“喜欢”就像两只蝴蝶一起飞来飞去,就是很浪漫的感觉。所以有一些孩子是有能力去讨论什么叫“喜欢”的。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心智障碍,就不问这些问题了。除了青春期的身体变化,他们对很多问题已经有想法了,默默地知道很多东西,只是不跟家长讲而已。我曾经跟一个孤独症男孩讨论过生死。聊天时,我提到捐赠器官,我分享了我想如何处理死亡后的一些事情。他马上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的父母会很伤心,你应该好好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能经常想死亡。我们鼓励他们表达任何内容,也收集他们的想法(比如对青春期、对身体成长的疑惑),再匿名地反馈给家长。
心智障碍孩子在性需求、性萌动方面跟普通青少年一样,表达喜欢的方式也和普通孩子差不多,嘴巴上表达喜欢,伸手触碰对方。我们上课时,要是哪一个志愿者哥哥、姐姐长得好看,很抢手的。有一次我们做练习,我问孩子,老师可不可以摸你的隐私部位?他说不可以。我又说,那个漂亮的志愿者姐姐可以吗?他说,可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这是危险的事情。
性教育课能讲到什么程度,家长的态度见仁见智。我们会预估教学内容是否超过大部分家长的可接受范围。比如针对青春期的自慰行为,我们能教的是,如何区分公共场合、隐私场合,怎么找到隐私场合解决需求。涉及到更细节的内容,例如如何达到兴奋感,我们不可能在班里教,因为有的家长会反感,或者认为班里的女孩子不适合听男孩子自慰的内容。但有的家长会在私下找我们寻求支持。
曾经就有孤独症的家长问我,老师你有没有“影片”,她要给我一个空的U盘拷回去帮孩子自慰。我说无论我有没有,我传给你我就犯法了。另一个孩子是中重度孤独症,语言能力很弱,上课时,家长需要坐在一旁引导孩子,该回答问题了,该和其他同学互动了。家长后来对我说,我很清楚我的孩子这辈子就这样了,他不可能结婚,他也不会知道别的什么事情。家长观察到孩子有生理需求,在房间里面自慰。家长就问我,可不可以买一个充气娃娃给孩子?我说当然支持,并给她提供了建议。
我有时候觉得,一些特殊孩子真的好幸福,遇到了尊重他们感受、照顾他们需求的家长。父母以快乐、幸福成长为目标,而不是说你要学会什么,你要考到什么学校。
好多年前,还有一个家长邀请我去指导他孩子怎么和媳妇性生活。这个孩子是心智障碍,家长帮他娶了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女孩虽然是普通人,但没有接受过性教育,一张白纸。我立即回绝了。我们是性教育老师,不是性治疗师,这不是我的工作职责。另外,我并不认可这件事,因为当中存在着不平等。
有一个女孩子每次来到少年宫上课,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看到我从柜子里拿道具,会主动说老师我帮你。但是她在知识上的互动很少,很多课堂提问她答不出来。她妈妈也问过她,孩子什么都讲不出来。我们有点挫败,不确定她掌握了多少。
直到她妈妈带她去上沙盘课,这门课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的。这个孩子堆了一个小沙丘。老师问那是什么,孩子说是乳房。后来她还堆了子宫的形状,这些都是我们课堂上展示过的图片。家长反馈说,孩子真的有听课。
后来,沙盘老师引导这个女孩子分享感受。她才说,她来月经了,她不舒服,她很恐惧、很害怕这件事。但孩子从来没有跟妈妈讲过这些。
有的心智障碍女孩来月经后,会很炫耀地跟我们说,老师,我今天来月经了。她妈妈跟她说过,来月经是因为你长大了,她就觉得她长大了,她不认为这件事不能跟别人讲。而在普通学校开讲座,我们问高年级女生是否来月经。即便现场没有男老师、男同学,她们也很害羞,多少还是有月经羞耻。
之前有一个帖子很火,一个孤独症孩子的妈妈说,女儿来月经,完全不能自理,她想切除孩子的子宫。站在妈妈的角度,我能够理解她,因为照顾一个心智障碍孩子真的很累。有可能这个妈妈掌握的资源很少,不知道怎么支持她的孩子;有可能她孩子的障碍程度很高,很难教;有可能是单亲家庭,一个人照顾。我们很难单纯地指责妈妈做得好不好,旁人没有办法体会她。我想更需要支持的是这个家长。
但是从《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角度来看(如第十七条保护人身完整性和第二十五条健康权),切除孩子的子宫很不可取,我个人不认为家长有权利做这件事。对有些家长来讲,他们想到的唯一方法,真的是摘除子宫。就单纯因为月经导致家长照顾压力大来说,如果有医疗介入、有经验的人给予支持,其实有科学的方式应对各种状况。
前段时间,一个家长和我们说,她也动过这个念头。她女儿的子宫发育不完全,没有生育能力,月经很紊乱。但是医生告诉她,如果拿掉子宫,孩子的激素分泌会受影响,要一辈子吃补充激素的药物。家长最后决定和孩子一起面对。
我们会教孩子理解什么时候用卫生巾,怎么拆封,使用后丢到哪里,突然来月经了怎么求救,弄脏了裤子怎么处理……有的还要帮助孩子不害怕经血。有个家长说,教卫生巾这件事让她觉得退回到一开始教孩子吃饭的时候。有的家长教会女儿使用卫生巾就花了三四个月,这算是正常的。还有的孩子真的教不会,家长只能到点去学校帮孩子换卫生巾。
有一位家长发现他儿子趴在女洗手间偷看,他和孩子沟通过,又送孩子来上性教育课。过了一段时间,家长说,苏老师,我们又发现新的问题了,以前孩子上网只搜“小鸡鸡”,现在他会搜生殖器的学名。家长为此很困扰,他觉得孩子没有进步。其实家长已经察觉到孩子的好奇,但不能因为搜“小鸡鸡”,出来的是“小黄鸡”的照片,就沾沾自喜;也不能因为孩子学到了更专业的名词,就觉得这不是孩子的进步。反而是家长应该同步学习,怎么正确地引导。
整体上,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比以前更重视性教育了。我们面试时,很多孩子能回答出什么是隐私部位、隐私场所,幼儿园会教这些内容,家长也会补充一些知识。以前,很多家长想先处理好孩子的康复训练问题、入学就读问题。还有的家长,尤其是孤独症父母,会花很多精力在“脱帽子”上——希望通过康复训练,让孩子趋向于一个普通孩子。结果,孩子到青春期出现问题了。
很多心智障碍孩子用手机很溜。疫情期间,我们曾以为他们使用网络上课是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因为坐不住,我们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跑掉了。但结果证明可以刻意训练,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吸引他们的专注力,需要有人一直在耳边不停地语言重复,或者让家长在旁边引导他们听课。
他们和普通孩子一样,刷短视频、短剧。于是新问题出现了,有家长发现孩子浏览过色情网站,或者加陌生人好友后,对方邀请裸聊。互联网对他们有帮助,也有危害。网络提供了很棒的科普片,但是网上的资讯有真有假,孩子们很难识别真伪,他们可能更偏向于看营销手段的内容。
有一次,一个心智障碍孩子在学校看到一位胖胖的老师,说你怀孕了。那个老师说我没有。普通孩子听到这句话就会结束对话。但我们的孩子说,不,你就是怀孕了。老师就有点“滴汗”了,我不是讲了我没有怀孕吗?那个孩子很大声地说,你要用避孕套。
家长查看孩子的手机后,原来是孩子对做妈妈这件事感兴趣,就搜索了“生育”。视频平台会猜你喜好,搜了几次之后,推送了避孕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在得到任何引导的情况下,使用了这个知识。你说孩子说错话了吗?没有,只是场景不对而已。
我们的柜子里放着避孕用品,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教他们怎么使用,最起码拿出来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孩子年龄太低了,只能让家长回去跟他们讲。
很多孩子还会和AI、智能语音聊天,聊的都是很日常的内容,今天发生了什么,我喜欢什么。因为心智障碍,很多孩子很难与朋友知心聊天。我们面试时也会留意跟这个孩子能聊多少来回,他们可能只会单线输出,不好奇别人的生活。而AI能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AI不会说你怎么说话不清晰,不会评价你的问题那么傻。有一个20多岁的心智障碍男孩问过AI,如果约女孩出去,去哪里是合适的。
有一个心智障碍女孩的家长检查女孩手机时,发现微信列表多了一个陌生人。聊天记录里有“老公”“老婆”的称呼,对方说,要看她的隐私部位,后面是视频电话的记录。后来,女孩告诉家长,在视频里裸露了隐私部位。
家长和我都在反思,是不是我们的关心不够?骗子先是聊天,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骗取一定的信任。孩子在家长、老师、朋友身上得不到的情绪价值,恰好在骗子身上得到了,就配合对方的要求。也许我们给孩子的耐性有5分钟,而骗子出于伤害的目的,提供了超过5分钟的耐心,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人对自己更友好。
有次上课,我问一个孩子,如果我用某某东西交换,让你脱裤子可以吗?孩子拒绝了。我又问,那用糖果交换呢?孩子马上脱。我没想到糖果的诱惑力那么强,我们不敢再做这件事。我们也跟家长讲,不要用条件交换的方式教育孩子,因为坏人也会跟孩子交换条件。
另一个新发现是,他们会用手机、小天才拍别人。有一个孤独症孩子会拍他觉得好看的志愿者哥哥、姐姐。哥哥、姐姐们很包容,但另一个ADHD孩子很敏感,他马上说不要拍,反复说了两遍就开始闹了。现在大家很注重隐私、肖像权,如果孩子在公共场合对着别人乱拍,又没有语言能力清晰表达时,就会发生误会。家长要提前和孩子讲好社会规范。
我们的课程有面试。我们会识别孩子的能力,观察是否有基础的表达欲望,是否存在攻击行为,是否抗拒性教育课程。我们遇到过非常抗拒的孩子,他/她觉得性是不能讲、很不好的事情。我们在课堂上展示不同年龄段身体发育的图画,有孩子整个人转过去,一个字都不想讲,甚至生气,我要出去。事后我们会了解抗拒的原因,有可能被伤害过,有可能是家长认为性是可耻的。还有的孩子捂着眼睛,透过指头缝看,你就知道他/她不是真的抗拒。
我们也会和家长面试,了解家庭对这门课程的迫切度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会征询这些案例能否运用到课程里,一起学习处理(比如有人邀请你看色情片是否可以,有人邀请你视讯时不能做什么)。有的家长把期待值拉得很高或者不合理,比如孩子出现了某个跟性相关的问题,他希望通过这门课,让孩子完全改掉那个行为;或者,孩子什么都学会了,不再产生任何相关的疑问,不再麻烦自己。这些家长从孩子确诊被磋磨了很久,他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教育心智障碍孩子的挑战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心智障碍孩子会认死理,行为很刻板,我当下想要这么做,我就这么做。家长困扰的是,我们已经讲过了,为什么他/她还会这么做?比如一个女孩一旦有需求无法被满足,会在教室嚷嚷,但另外有的孩子,一旦听到突然的尖锐声音就很敏感——有个男生会非常焦虑(他的家长说这时要给他一个毛绒玩具来缓解焦虑),另一个孩子会捂起耳朵。嚷嚷的女孩的妈妈在教室外听到,会马上冲进来安抚孩子,跟我们说老师要不你先答应她。我们没办法,只有答应,但一年课程结束后,孩子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会加深她的刻板行为。
之前有一个成年孤独症男孩独自坐旅游大巴,和前座的女孩交流很愉快。参观景点的时候,他看到女孩在用一款软件,说你也用这个。女孩回复,这不是废话吗?男孩情绪崩溃,质问女孩是什么意思,女孩被吓哭了。男孩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对,大喊着抱歉。因为没有得到女孩的回应,他就回到大巴车上把窗帘扯下来。
还有个学生,一米八几的大男孩,每次来教室都说苏老师好,跟每一个人热情地打招呼。有一天下课后,他一个人站在马路对面,我们向他挥手,问他怎么还没有回家。他好像看到鬼一样,马上跑掉了——没有人教过他在大街上看到老师要怎么回应。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确定,但是心智障碍孩子一定要“确定”,他们有很多刻板行为,很容易陷进去,很纠结,一定要你给一个所以然。我们需要让孩子学会拒绝、接纳拒绝。
还有家长教会孩子坐地铁,但广州的地铁线好挤,他孩子可能碰到其他人,被别人误以为是色狼,故意骚扰。现在的讨论空间很容易变成敌对,有的事情很难理清,这时候孩子要怎么帮自己?
我们希望性教育课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融合,减少他们在公共场域中不恰当行为的可能(比如脱裤子、自慰),以及当发生相关问题时,他们能做什么(比如寻找洗手间等隐私场所,求助于家长)。但我们很难预测孩子会遇到什么,很难穷尽所有的状况,所以亲子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关系良好,家长是孩子信任的人,那么无论孩子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主动分享。
公众对心智障碍人士的接纳也要一起努力,不然推动社会融合只是空谈而已。有一个ADHD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情况。ADHD孩子的智力没有受损,有社交欲望,但没有社交技巧。他们的专注力不足,接收的信息量爆炸,很爱接茬。他们提问时,他其实知道那个答案,他只是在挑战规则和底线。结果,有天老师问孩子,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孩子很受伤。我听家长转述的时候,我也觉得好伤心,很生气。
有的家长会瞒着孩子(病情),有的会积极地跟孩子讲,解释为什么他/她需要去做康复训练。一个罕见病孩子知道自己的情况,当她出现某些行为,比如偷吃、生气,她会说这不是我想的,这是疾病导致的,就不会自责了。还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班里说,某某是孤独症。因为他在学校里被别人这样说。我告诉他,不要这样评判一个人。
这几年我们还观察到,普校里普通孩子的情绪问题比较严重,或者在家庭里面受到伤害,他们会转移欺负的对象,欺负特殊孩子。有一个学生把学校里一男一女两个孤独症孩子叫到后楼梯,让孤独症女孩脱掉衣服。有人来咨询我,我建议两个孤独症孩子去看心理医生,如果状况可以,再去补充性教育的知识。后来女孩来上我们的课了,男孩没有。有次课后,我和女孩聊天,她断断续续讲起那件事。她说,这件事是不对的,对方不可以这样做,我也不可以这样做。女孩的状况良好,我想是她妈妈对她的支持和关注很到位,没有责骂她。
好多年前,我去某个省会城市,当地只有一所特殊学校,那时候广州每个区都有。各区也有招收心智障碍孩子的职业高中,要求有智力障碍残疾证。而在办不办残疾证这件事上,能看出家长们的纠结。家长觉得,办残疾证等于盖章,这个孩子就是智力残疾。有的父母一方接受现实,另一方或者爷爷奶奶不接受。
不愿意办证的家庭失去了入学机会,但他们可以在普校随班就读,参加中考。只是,很多孩子就读中学后出现情绪障碍,确诊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这和青春期有关,也和中学的环境不像小学那么包容有关。
在广州,你确实有机会在公共场合看到一些残障人士。省博物馆、大剧院有时候会给少年宫提供一些公益票。还有一些社会活动,欢迎孩子们去参加,家长们愿意(也有体力、精力)的话,就带着孩子赶场。然而,依然有很多残障人士完全留在家里,没有办法使用公共服务。
针对“福利断崖”的世界性问题。从医疗和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看,年龄越小,康复资助的价值越大。比如在广州,年龄越小越容易申请到康复资助,每个月有1700元,14岁之后就没有这项资助了。但是从社会融合的角度,14岁之后的余生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广州的一些机构、家长也在推动针对成年心智障碍者的服务,比如就业、养老。
我也听到一些家长说,小时候砸锅卖铁也要带孩子去做康复治疗,最夸张的半年烧了20几万。广州最普通的康复费用是每月7000到1万元,从3岁开始介入治疗,一直到11岁左右,家长发现原来孩子康复不了,会非常失望。等孩子中学毕业后,没有学校再招收他们,也没有任何社会服务可以使用,家长也没有动力再带孩子到社会里面,他们只能在家里了。所以“福利断崖”问题,一是社会支持的部分(减少乃至消失),再是家长在过程中消耗太大了,无论是经济消耗,还是精气神的消耗。
我做这一行会有挫败感。因为性教育更多是运用到实际当中,我不确定我讲的知识他们都接收到了吗?后来,有家长跑过来告诉我,老师,你的课是有用的时候,我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孩子遇到了特殊状况,用到了我们教的内容。这个感受反而是我不想要的。我又转念想一下,幸好孩子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幸好他们参加过性教育课程,父母后续给了更多的支持,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帮助自己。所以,我也不停地在自我调整中。
有人说性教育是从出生到坟墓的教育,它不是孩子唯一要学的东西,但是孩子必须要学的东西。与性相关的行为、问题,可能是心智障碍孩子融入社会的绊脚石。他如果突然当众脱裤子,家长不知道怎么支持和处理,周遭人不知道怎么看待,家长会觉得有压力,要求孩子以后不要出门。他们待在家里,社交能力会退行,慢慢变得越来越呆滞。
当你能够全面地去看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特别的事件,就像普通人摔了一跤,你可以怎么办就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