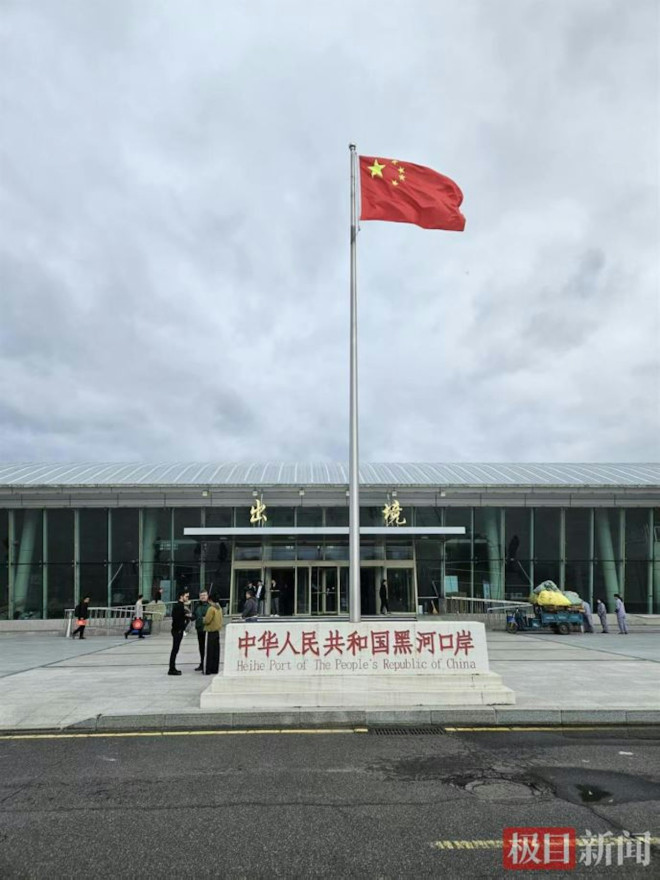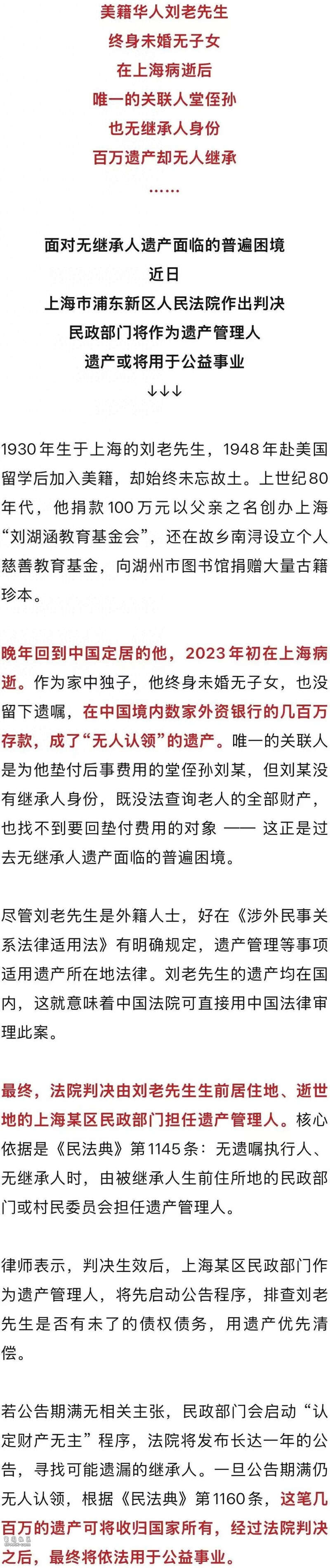博主记录旱灾中的村庄,老人对镜头苦笑 ...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摘要:这是一个多省遭遇大旱的春天。4月下旬,up主赵玉顺和贞贞一路开车,用影像记录下多个省份的旱灾样貌。
在江苏泗洪,一个农民在麦田伸出腿比划,往年麦子应该长到大腿,今年还活着的麦子,也只长到了膝盖。
在安徽,一个农民用“电三驴”的电瓶接水泵,算着一笔让人心酸的账:只浇一半的田,剩下一半离水源太远,浇水更费劲更贵,放弃了。
在河南信阳,水稻插秧晚了约20天,一个承包了400亩地的农民已经73岁,说起自己的年纪,只能无奈苦笑。
在广西,村庄里的池塘第一次见底,连耐旱著称的仙人掌都枯死了,而人们还在将溪流最后的一滩滩水抽进稻田。
这对90后搭档已经在拍摄农村的路上奔波了数年。他们都出身农村,当意识到城市不属于自己后,将镜头和麦克风对准了农民。20多分钟的视频没有加速、没有滤镜,只有旱情下的庄稼,以及一个又一个农民的讲述。
我们和赵玉顺聊了他所见到的干旱,以及为什么记录这场干旱,以下是他的讲述:
大旱的样貌
我们对这次旱灾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清明节出发,我们原计划拍中部东部的经济作物。在江西、安徽拍完春茶采摘,一开始进入江苏,在车里还看不出干旱,麦子依旧绿油油的。只有到了地里细看,你才会看到,麦子的穗粒数是偏少的。
第一个告诉我旱情的是江苏泰州一个大姐,她和丈夫承包了两百亩地,说今年要亏本,“半年没下雨了”。我相信她这样的大户肯定很焦急,但她言语平静,只是看起来有些沮丧,没说几句,又去浇农药了。
那天是4月22日,全国气象干旱图里,泰州是深红色,代表特旱区。但哪怕这时候,我们也只以为是场普通旱灾。一方面,这几年我们拍了不少旱灾、涝灾,钝感了、麻木了。另一方面,我们想着江苏河网密布,池塘也多,虽然干旱,是不是村民可以低成本浇灌,问题不会很大?
但是越往西,我们看到的情况越严重。到了宿迁泗洪县,走到淮河边上,我从没见过这么惨烈的麦子,大概三四成麦子肉眼可见地差劲,瘦小、枯黄,叶尖被烧成了褐色,像秋天落叶一样脆,稍微一搓,里面是空的,掉落出麦粒碎屑,相当于绝收了。
晚饭后,一些农民出来散步,向我们确认了旱灾的严重。有一个大爷叹了好几口气,给我翻出一小片(麦子),已经到了绝收边缘。活着的长得也不好,他伸出一条腿比划,说往年麦子应该已经长到大腿根部,现在才长到膝盖。如果不是在田头,你想象不到还有这种衡量旱灾的方式。
旁边就是淮河,但几个“散户”农民都告诉我,他们没有浇水的打算。一个大姐独自在地里给青豆除草,跟着条收留的瘸腿流浪狗。这原本是块油菜田,大姐2月份就意识到雨水少,改种了青豆。浇一次青豆,她要从淮河背六桶水,她还有点麦子,但早就放弃了,说“就随它吧”“只能等(雨)”。
说起来很心酸,卖粮食是不怎么挣钱的,一亩麦子收成好也就挣几百块,对自种几亩地的“散户”来说,抽水就不划算了,哪怕是在淮河边。这让我很触动,决定把旱灾当一个专题拍。
2025年4月22日江苏泰州兴化市,冬春连旱导致水渠旁的土地都已干裂。讲述者供图
我们继续往西开,旱灾的样貌越来越充分。到了安徽,一段几公里的国道上,我看到至少三个农民在浇水。前两天当地做了人工降雨,但水肯定还不够。这里同样不属于高标准产粮区,没有配套浇灌设施,农民是自己用电瓶接水泵在抽水。就是“电三驴”用的电瓶,在农村里家家有这样的电驴,收获季也用它运粮,真的相当于新时代的驴,但哪怕自己改装加了大电瓶,也就能浇两小时。
对“散户”来说,浇水还是不浇,算的是综合账。安徽一个大爷特别有代表性,他一共8亩麦子,他一边浇水一边跟我说,他只浇4亩,还有4亩不浇了。离水源太远了,那意味着你需要更长的水管、更多的电费,不划算了。
到这时候,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旱灾的严重。我们还计划去湖北拍小龙虾,为了记录旱灾,特地先绕去了河南信阳市,想看看不同作物的情况。也是在那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这场干旱也许是历史级的。
苦笑的农民
4月26日上午,我们到河南信阳市商城县,正赶上他们在插秧苗。这很不正常。往年应该二十多天前就插下去了,但今年没水,一直不敢插。
这天,水库放水,他们赶紧挑着秧苗种下去。所以旱灾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季农作物的收获,还有下一季农作物的种植。
旱灾对种植大户打击最大。一个姓朱的大爷种了四五百亩水稻,焦虑得整张脸都紧绷着,相比一些“散户”,他的语气明显更愤恨,不停摇头,说去年一年几乎就下了一场大雨,其余都是小雨,“小雨有个啥用啊”,“前段时间下个雨,还没下透就停了”。
朱大爷头发一茬茬地白了,背也驼着,聊不了几句,又挑着一担几十斤重的秧苗要去田里了。临走前,我问他几岁了,他说73岁,说着就笑了,留下一句,“不干又能怎么办”。
我只能理解为一种苦笑吧。我想起了我爷爷,很久之前我问过他,你要做到什么时候?他在那里挖土,我问他要挖到什么时候,他说,挖到把自己埋进去为止。
过去三四年,我们有一半时间都在农村拍作物、拍农民,走了全国一千多个村镇,记录过很多次旱灾。很多场景是类似的。作物枯萎、减产,小心溺水的牌子后面,是彻底干枯的河流、池塘。在四川,我第一次见到竹子竟然会枯死,会变成土黄色。在果园,我看到柑橘被烤黑了,一个大哥还在浇水,希望能保下来树,树要是死了,再种又得好几年。
从东到西,农民面对天灾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他们从来不会直接说我好难过、我好痛苦,不会的,更多时候,只是默默想办法去拯救它。
73岁的朱大爷告诉我,当地上次那么大旱灾,还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他才十来岁。
我确信这在当地是一个事实,因为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说。几十公里外的山上,一个茶农也这样告诉我。他自己60岁,没经历过,但他80多岁的父亲告诉他,上世纪60年代才有这样的干旱。
当地种的是信阳毛尖,我们专门去看的,新闻上说,有茶农专门运了一车水上去浇,这说明茶叶还是值钱的,值得救的。但山上的茶农大哥告诉我,今年茶叶减产了六成,摘茶的、种茶的、制茶的今年都没搞到钱。不仅产量减半,雨水湿不了地,茶叶长势不好,季节过去,也不值钱了。
为了更完整记录下今年旱灾,开车回湛江前,我们还去了广西。之前就有新闻说,今年广西干旱六十年一遇。我们想,这次旱灾严重程度和它得到的关注是不匹配的。
(注:据《中国气象报社》5月16日报道,这次干旱在广西、江苏、山西、甘肃等省份呈现极端性。在广西和江苏,自1月1日以来的平均干旱日数均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在陕西和甘肃,自3月1日以来,两省平均降水量均偏少五成以上,分别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和第二少。有学者近日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表示,“目前的判断是,这次旱情已经产生了一次跨区域跨流域的特大气象干旱事件。”)
我们去了钦州,看到情况确实非常严重,一个阿姨说,她嫁过来三十多年,从没见过村里的池塘干过,但今年已经见底了。在都安县百旺镇,我们看到玉米奄奄一息,甚至有仙人掌都枯死了、风干了。
在之前的几个省份,我们听到至少生活用水有保障,但在广西一个山上,五一假期回家的学生告诉我们,抽上来的水很紧张,可以洗澡,但洗衣服不够,用过的水再拿去冲厕所。
山脚,溪流石头裸露,水成一摊摊了。这种情况下,有阿姨在抽水去下秧苗。
对“散户”农民来说,粮食卖不上价,可以考虑不救。但不管怎样还是尽可能要种下去的,哪怕收成不好,至少口粮可能有了,不用买了,买和卖也不是一个价。
(注:在赵玉顺和贞贞五一期间拍摄后,广西迎来了降水。5月20日,广西决定终止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通知显示,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广西旱情得到显著缓解。
另据中国气象局网站消息,5月底,西北地区东部、河南西部和南部地区预计有较强降水,气象干旱阶段性缓和;其余旱区干旱仍将维持或发展。)
2025年4月26日,河南信阳商城县,大旱导致水稻插秧时间相比往年推迟二十天。 讲述者供图
给农民一个麦克风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旱灾。2022年,我们第一次长途拍摄,就是在四川几个县,拍了长江流域的大旱。
当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城市里的新闻,乐山大佛露出、嘉陵江见底,这让我们决定要到农村去拍下大旱,记录下农村的遭遇、农民的声音。
今年,我们拍摄的4月份,互联网上依然很少看到关于大旱的新闻。5月4日,我们的视频发出来后,一个苏州IP的留言说,苏州有干旱吗,完全没有,你别乱说。
城市里的人很难感受到旱灾对农村意味着什么。虽然江苏现在可能有所缓解,但在当时,苏州就是全国干旱重灾区,他却对一切毫无感知。我觉得这很割裂。
2025年4月27日,安徽蚌埠五河县浍南镇,村民利用三轮电动车的电瓶抽水浇灌小麦。 讲述者供图
即使在农村,你会发现小孩子普遍对旱灾缺乏感知。他们玩手机、看视频,该干嘛干嘛。我很理解这些孩子的状态。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未来在农村。
我自己就是这样,很小的时候,长辈就跟我说,你这双手是要去拿笔的,不应该是拿锄头的。于是我信以为真,自己应该要去更大的城市,要去北京上海,一直往外走,甚至走出国。
2017年从一个普通二本毕业,我在很多城市工作过,三亚、深圳、北京、广州,越来越觉得,我和城市是疏离的,城市的花花绿绿和我没有关系,我的根不在城市。
我做过记者,接到热线,反映停车位矛盾。采访完业主和物业,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回出租屋,路上遇到一辆汽车,按喇叭“嘀”我,那一瞬间我很生气。在这座城市,我没有车,没有房子,却在帮别人解决停车位问题,这很荒谬。
后来干写宣传稿的外包工作,越写越觉得沮丧,还拿着最低的公积金。在一个出租屋里,我和贞贞决定,去拍自己想要拍的东西,“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
我们从珠三角的小城拍起,逐渐走向全国的农村。农民看起来是沉默的,但当我们拿着摄像机,把麦克风送到他们面前,他们是愿意表达的,而且他们的话是有力的、生动的。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呼吁,2023年在河南拍烂场雨,农民们抢收完麦子在路边晒,一个大哥骑着拖拉机路过说,“如果你是记者,你这次才看到我们农民真正的生活”。
还有些表达更深刻,关于农民的身份、农民的保障。比如在广西,一个砍甘蔗的大叔说自己太脏了,不好意思上镜,我说劳动最光荣,他说,“劳动是最光荣,但你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劳动”。
又比如在湖北,我们拍从淤泥里挖藕的人,这活非常累,干久了还会得风湿炎,抬不起胳膊,哪怕收入不低,也没有年轻人愿意干。但一个59岁的大哥专门从外地过来挖,十多年如此。我问他是不是再干几年也要退休了,但那个大哥说,“老百姓死不了就往死里干,一停下来就没得生活。”
我觉得光从这些话,城市里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天灾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了。而我们希望至少记录下这些话。
2025年4月26日,河南信阳商城县,终于等到鲇鱼山水库放水后,村民用水管从水渠引水。 讲述者供图
记录的意义
好多人问过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农村?还有人问,记录的意义是什么?你所做的这些记录,能起到哪些实际的作用?就比如说干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看见了,然后你可以帮农民多浇一点水吗?你可以给他提供每个人每家每户一亩20块钱的抽水补贴吗?
这真的是灵魂的拷问。问的人未必是恶意,我觉得他是面对自己觉得不合理的或者不公平的,也想要寻找一个答案。
就连我自己也问过,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那时候拍摄,我和贞贞轮流打工、接外活,支撑账号的运营。现在情况好一点了。这两年账号逐渐有些影响力,我们也接到一些商单,覆盖掉拍摄支出,去年可能还有点盈余。
虽然我们的经济状况还是很糟糕,车贷没还完,春天出去拍摄两三天才住一次宾馆,到现在只有一台相机、一台无人机,但我觉得当下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能够自主决定拍什么、表达什么。
不拍摄的日子,我们住在贞贞老家,湛江一个小镇,和她奶奶一块。我们收养了一只小狗,早上出门遛狗,然后去菜市场里面买菜,永远是菜场里最年轻的人。下午工作,我负责文案、她负责剪辑,谁也不干涉谁。
我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枯燥的。我们现在觉得城市生活才是无聊的、单调的。在公交车上,我甚至知道有一个背蓝色书包的男孩下班时间是下午6:30。一位都仿佛安排好的,像是楚门的世界。可能你周末醒来,想吃火锅了,中午就去海底捞。然后你想着要爬山,再去迪卡侬买双登山鞋。到了晚上,去万达影城看个电影。这样的生活可能发生在乌鲁木齐,也可能是温州、昆明或者哈尔滨。
有时候我在拍摄途中醒来,都忘了自己身处哪个城市。一样的立交桥,一样的车水马龙,一样的连锁品牌。大家刷一样的热搜,上面反反复复都是同一批人,喜茶上市一个新品,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在品尝。
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
而当我们去到全国各地的农村,你能感受到区域的差别,四季的差别。当你和一个又一个农民交流,听他们的故事,会更理解这片土地,也更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人生。
我们没有能力去提供解决方案,更不要说改变什么。但我觉得记录本身就有价值。至少,它可以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识。而且记录是第一步,连这一步都做不到,农民没有被听见、被看见,怎么会有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