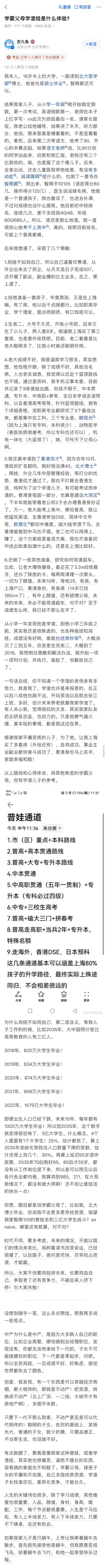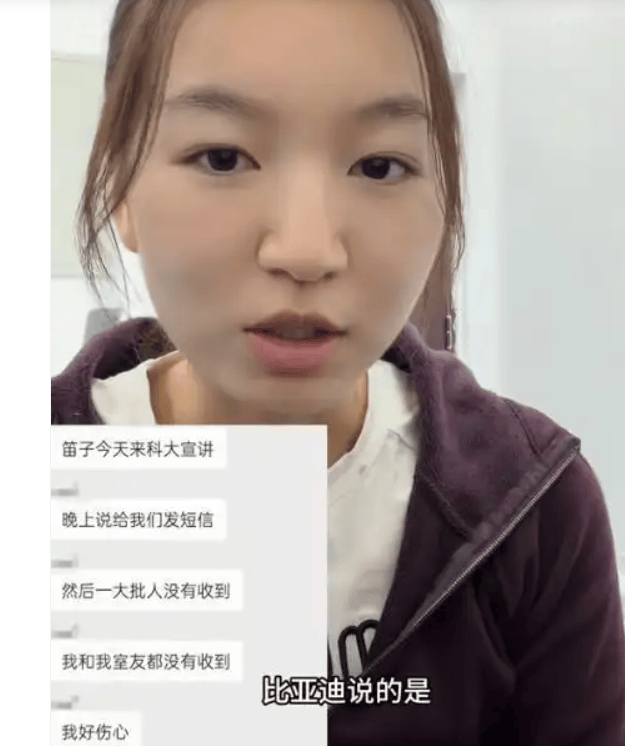上海出手背后,多少家长因作业而狂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25年5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优化上海市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提高作业育人水平的通知》,其中再次明确了2021年“双减”政策中的要求: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上海市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10条负面清单/图源:上海市人民政府网
辅导作业看似日常,却是愈发显著的家庭矛盾来源。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南风窗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谈起辅导作业,家长们各有各的头疼,有人感觉自己“快被气死了”,有人真的因一时气急被送进医院,还有家长辅导作业几年之后,被诊断出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很多家长不愿打骂孩子,却一次次在教育孩子引发的冲突中失去理智。
家长的抱怨和相关政策的一再强调,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件事:辅导作业、教育孩子的日常,为什么成为困住家长和孩子的牢笼?
01
作业战场
因为要每天督促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完成作业,徐月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被气死”的家长?
她的情绪随着女儿的作业完成情况而变化。有时候,女儿在学校完成了大部分作业,回家后只花十几分钟就写完了作业,徐月会开心地表扬她。更多的情况是,女儿没有在学校完成作业,回家后也一直拖延,完成后的作业里还有不少错误。徐月必须给女儿讲题,讲着讲着她就会生气,甚至气到“喘不上气来”。
辅导作业考验着家长的耐心。遇到做错的题、读不对的单词,徐月有时候要反复讲三五遍,女儿仍然听不懂、读不会。另一个妈妈也为此头痛,她会先教女儿做一遍,然后问女儿“懂了吗”,女儿回答“懂了”,但等到女儿自己做的时候,她还是不会。
孩子的态度还在进一步刺激家长。徐月的女儿没听懂,但还很犟,觉得是徐月讲得不对。她会不服气地顶嘴:“就这样!”“那怎么了?”原本就已经不耐烦的徐月,会因此更加气愤,“把我逼到一个崩溃的点”。
在辅导作业时,孩子的态度也会刺激家长/《学爸》剧照
情绪的升级有时不受理智控制。徐月也打过女儿,“直接砸屁股墩上,真的是往死里砸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发)火了,我给她朝脸上就是一巴掌”。
她知道这样不对,也心疼孩子。打完她就跟女儿道歉,解释自己为什么情绪崩溃,检讨自己不应该这样。
作业成了亲子矛盾的主要导火索。而家长们都发现,发怒是无效的,辅导作业无法帮助孩子学习,还会产生诸多反效果。
徐月能感觉到,自己的督促没有给女儿的学习带去多大的影响。从女儿上小学起,徐月就会陪着她上网课,女儿很容易走神,要么是摆弄桌上的玩具,要么是目光飘去了别的地方,每隔几分钟,徐月就需要提醒她看屏幕。到了三年级,徐月依旧需要不断提醒女儿完成作业。
孩子写作业时有时候会走神/《小舍得》剧照
而家长的怒火,换来的往往是孩子的对抗。
家长冯欣过去也常常因为写作业对女儿发火。她至今还记得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她叫女儿写字,只是写几排简单的数字,但女儿不肯写。冯欣又说了几次,拿起衣架就往女儿的屁股上打过去,皮肤上的红印很快浮现出来。即使如此,女儿仍旧不肯写,也不哭,“(她)也没服输的”。
“我也是看得到的,我用我的‘镇压’没有把她压下去。实际上我们(之间)就没有胜利者,我也是失败的,她也是失败的。”冯欣说。
亲子关系被扭曲了。在气头上的时候,徐月摔女儿的书、摔作业本,还撂狠话,“我也养不了你了”“咱俩今天就到此为止”。女儿学会了看徐月的脸色,观察她的眼神,如果徐月教育她的时候提高了音量,女儿就像是有点怕她。
辅导作业导致亲子关系被扭曲/《小舍得》剧照
徐月也会害怕,她害怕这场围绕作业的“战争”,把自己和女儿都逼出病来。有三四次,女儿自己把作业本摔了,然后在徐月面前尖叫大喊,“我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徐月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和情绪,也在慢慢转移到女儿身上。
其实徐月并不愿意管女儿的作业。她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偶尔还会加班。下班后她要带女儿上游泳课,一直上到晚上八点半才回家。她已经很累了,只想看手机、睡觉。但不行,她还得催促女儿写作业,有时候要一直等到十一点,才能真正躺上床睡觉。
更重要的是,她担心自己的“辅导”并不对。即使是拼音、汉字笔画这些基础知识,她每次也要先上网查一遍才敢讲。女儿上三年级之后,数学题开始变难,有时候女儿拿来问徐月,她感觉自己也被题目“绕进去了”。徐月买的学习机也不太好用,有时候,它会直接显示答案,女儿就会直接抄,不去思考过程。
但这场“战争”很难就此结束。因为女儿的拖延、不专注,徐月仍然认为督促作业是必要的。她进退两难:“你不督促她就完成不好,你说你又能怎么办呢?”
02
家长的作业
事实上,2021年开始推行的“双减”政策,已经明确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其中也强调了作业指导和监督的职责,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而对于剩余的作业,则是要求“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
即使如此,家长们正以另一种形式,被迫卷入到孩子的作业当中。
即便开始推行的“双减”政策,家长还是会被迫卷入到孩子的作业当中/《追爱家族》剧照
作业的布置与完成,都依赖于家长的手机。徐月的手机里有两个app与女儿的作业有关,数学老师用“班级优化大师”,英语老师用“外研U学”。老师们把作业发到app里,再由徐月告诉女儿。女儿把作业完成后,还需要徐月拍照上传到app里,供老师批改。
“现在什么作业都离不开家长。”徐月说。她的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有时候徐月需要出差,她要么打电话告诉女儿有哪些作业,要么把女儿和她的作业都托付给朋友——朋友的手机里也安装了这些app,帮女儿拍照上传。也有几次,她没找到人帮忙,只能打电话告诉老师,因为自己在出差,女儿没办法上传作业。
更常见也更简单的“负责”,是要求家长签字。冯欣能感觉到签字这件事隐含的压力:“你签了字就要负责,她做都没做,(或者)她全做得不对,你咋签字?”
感到压力的家长并不少。据央视新闻,2020年,江苏一位家长在短视频里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以表达对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的不满。澎湃新闻则在2024年报道过一则新闻,浙江台州一位家长在小学门口下跪,大喊“校长,我求你了,取消钉钉”。后来当地教育局回应称,该事件与钉钉打卡并无直接联系,而在该条新闻的评论区里,对家长群、班级群、打卡深有共鸣的家长们,留下了超9000条讨论。
家长在校门口下跪,大喊“校长,我求你了,取消钉钉”/图源:大河报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赵同友在论文中用“全景敞视监控”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将家长困住的系统。即通过班级群、相关应用软件这种便捷、低成本的途径,教师将家校沟通、互动变得更为日常,将家长从过去的家庭养育者,转变为教师任务的执行人、子女学习的辅导者。
“家校沟通的界限消失了。”赵同友进一步解释说,“通过微信或者钉钉,学校可以无界限地‘监控’孩子,而家庭生活也已经开始以学校教育为中心来运行。”
比如,不少老师会告诉家长,在家里也要像老师要求学生一样要求孩子:回家就先完成作业、写作业时不要来回走动等等。
而与“监控”同时存在的另一层压力,是学校对家长的评价。在这一评价体系里,“好学生”与“好家长”是被绑定在一起的。
在徐月的“班级优化大师”app里,记录着女儿这周拿了几朵小红花。如果徐月不能上传作业,或是上传的作业质量不高,都会影响小红花的数量。一二年级的时候,老师会按照学生的表现排名,给靠前的孩子发小礼物,排名也会显示在教室门口的显示屏上。那时候,徐月的女儿也会在意自己的表现。
好家长也会得到荣誉和表彰。家长们都提到,每学期的家长会上,都会有家长来分享自己家校共育的经验。冯欣对一个妈妈印象深刻,她的孩子在班里年龄最小,但进步很快。过去,孩子英语口语不好,害怕表达,现在已经能自信地和人沟通、上台讲话。冯欣了解到,孩子妈妈没有工作,全职在家辅导,寒暑假还能把孩子带出国见世面。
每学期家长会都会有家长来分享自己的教育经验/《小舍得》剧照
但冯欣做不到这样。“我们没时间,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家庭生存上面。”她觉得,比较起来,自己只能说是一个及格的家长,“差了很长一截”。
在赵同友看来,这种评价和表彰就像“广场示众”。而当孩子的优秀与家长是否合格直接挂钩,也给家长带去很重的道德压力。
压力之下,家长却很难有别的选择。徐月常常和朋友吐槽作业的事,却不敢直接找老师沟通。她担心老师不满,针对自己的女儿,同时也知道老师有自己的苦衷,不愿意再去给他们添麻烦。“说实话,现在很多家长的心理都是在等冒头的。”
曾经有一个家长“冒头”。徐月记得,有个家长自己也是老师,他嫌学校布置的作业太多,孩子又比较磨叽,有一次就没让孩子做。第二天,老师直接在班级群里点了孩子的名,说他的作业没有写,让孩子回家后补上。
“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很尴尬了?”
03
摆脱系统
被系统困住的徐月,害怕自己的孩子会落后。她能感觉到家长之间的“卷”,开家长会的时候,也有家长会觉得孩子作业不多,还说自己会给孩子布置其他的作业。徐月担心女儿的学习跟不上,又无力辅导,于是开始考虑给女儿报课外的数学辅导班。
这种焦虑,反映出家长难以摆脱系统的根本原因。赵同友告诉南风窗,《爱、金钱和孩子》一书分析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家长教育参与情况,以及他们的教育焦虑,最终总结出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收入分配不均衡,而教育回报率又很高,它就会导致父母对教育十分焦虑,且积极地介入到子女的教育当中。
国家的经济收入分配不均衡但教育回报率很高时,会导致父母对教育很焦虑/图源:unsplash
“这一点在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表现得都很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收入分配是不均衡的,基尼系数比较大。”赵同友说。在这一背景下,家长的“鸡娃”其实是一种理性、清醒的选择,“他们对自己的子女如何能在社会中获得优质的资源,如何获得幸福,他们是看得清楚的”。
但与此同时,也有家长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做一点摆脱系统的尝试。
冯欣尝试让作业真正变成孩子自己的事。她后来有了第二个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她反省自己,慢慢纠正和孩子相处的方式。过去,她总是用命令式的语气,指挥孩子做题,现在她学会让孩子自己读题、自己写。如果她想要检查作业的完成情况,还会先问孩子:能不能给妈妈看看?
黄婕的“放手”则更加彻底。她说自己是个有点“懒”的家长。从女儿上小学一年级起,黄婕从来不检查她的作业,也不会给她讲题。老师要求家长签字,黄婕会让女儿自己签,有时候要听女儿背诵,她不会对照课本检查,而是直接听女儿背,女儿说背完了就背完了。家长会上,老师经常强调家校共育,“听听就好了,回来还是按照我的(做)”。
应该让作业变成孩子自己的事
这种选择基于她的观察。女儿两三岁的时候,黄婕就发现她喜欢关注路边广告牌上的字,认识的字变多之后,女儿可以安静地读自己喜欢的书,不受外界的干扰。这让黄婕觉得,自己不去过多地参与女儿的学习,可能更好。黄婕的丈夫也赞同她的观点,于是,包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内的整个家庭,都不会去辅导女儿的作业,除非她自己提问。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黄婕能看到,现在的孩子比过去的自己更辛苦。
她在四川省一市级教育局工作,身边也有很多当老师的朋友。黄婕常常从朋友那里听说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学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患上抑郁症,放弃读书回家休养,也有的学生压力过大,在毫无征兆地情况下跳楼。
“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现在的小朋友受的打击太少了,才这样承受不住压力,我就说你们要去看看现在小朋友的卷子,真的很难做。”黄婕说。
现在小朋友的学习难度更大/《追爱家族》剧照
她对女儿的语文试卷印象深刻。小学五年级的一套试卷里,四大名著中每一本的内容都被考察到了,学生还得对目录、内容情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回答题目。但在黄婕看来,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感兴趣的可能只有西游记,三国演义也不一定都能看完。
青少年心理社工张晗主要服务厌学、弃学的青少年,已经有大约七年的经验。他也观察到,孩子的学习压力在不断地被前置。例证之一是,他服务的青少年越来越年少。2019年,张晗接触到的大多是大学生或高中生,现在则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找到他,其中有很多初一、初二年级,甚至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厌学的背后,存在一种认知错位。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希望通过教育为孩子的未来生活赢得确定性,比如好大学、好工作。而张晗观察到,这套逻辑在很多孩子那里已经不成立了,不少孩子告诉他,他们也会在网络上看到“社畜”“996”一类的讨论,家长的“劝学”,有时候是行不通的,“(孩子)他们更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
意识到问题的家长,比起在系统中继续内卷,选择把“育人”放在前面,让孩子的自我生长出来。
把“育人”放在内卷前面/《小舍得》剧照
黄婕虽然“放手”,但并非不关心教育。她给女儿定了一个基本目标,各科考试成绩要达到95分以上。黄婕观察过,这个目标对女儿来说不算太难,达成目标,她基本上一直稳定在班里的十几名到二十名——在小学阶段,她不希望女儿为了“拔尖”付出太多。
学习之外,更多的时候,她希望让女儿理解一些“大人的道理”。黄婕和女儿约定,只有周末可以玩手机、看电视,如果成绩没达到95分,玩耍的时间就会被扣掉,这是“底线”,黄婕告诉女儿“要有自己的底线思维”。每次女儿犯了错很委屈,黄婕也会教育她,“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是“要学会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现在,黄婕还不知道女儿能不能真的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但至少,培育孩子独立的自我,让孩子学会找到自己的路,对家长而言也是一种解放。比起使劲拽住孩子,把她拉到一个更高的地方,黄婕更希望孩子是自己愿意去。
这同时意味着,家长要能够接受孩子的“跌落”。黄婕和丈夫都考虑过,如果以后女儿真的学不动了,他们也愿意让她去职业学校,学一门技术。这种很多家长不愿接受的选择,并不影响他们对女儿的爱。
家长要能够接受孩子的“跌落”/《小舍得》剧照
因为在黄婕眼里,女儿比自己还要厉害。“不管是考试、做作业还是读书,各个方面都比我厉害。所以我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她能做到?她已经做得很好了。”黄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