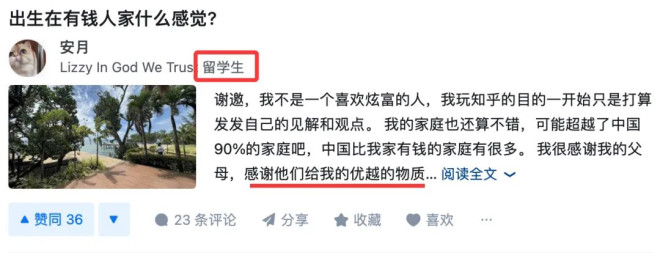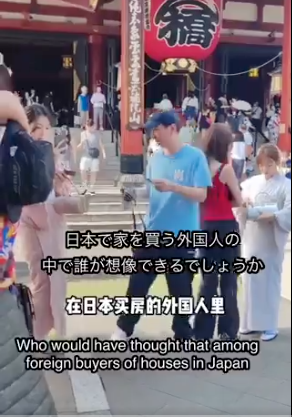70多年前,那些润得飞快的上海宁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本篇继续写润学人物,但视角将聚焦于上海人。前两篇共计14位人物,竟有6位是上海人,将近一半!本篇将增加3位商人代表的嗅觉,与上述6位上海人(倪匡、杜月笙、李政道、胡蝶、张爱玲、潘柳黛),合成一篇《上海人的嗅觉》,以兹纪念。
在50年代的香港(专题),上流社会喜欢听的是英文歌和带着上海情调的国语歌。在那时的香港影视作品中,说上海话的角色永远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那会儿要是在在文化圈、电影圈混,要是不会几句上海话,那可就亏大了!
那么海派文化在香港如此火热呢,原因是在70多年前的历史洪流中,上海人凭借独特的嗅觉,南下香港,他们不仅迁徙了财富和文化,也带去了上海的灵魂:精致、务实、永不墨守成规。
同时,这些上海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危机中,总有另一种可能。这正是上海人那独特的嗅觉——一种对变化的敏感,一种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一种对机会的精准把握。
邵逸夫:
从上海滩到“东方好莱坞”
为什么上海话在早期的香港娱乐圈地位这么高?
答案藏在TVB的创始人邵逸夫身上。这位在上海发迹的娱乐大亨,早年直接把上海话定为公司内部沟通语言——郑佩佩回忆当年拍戏时的趣事:"邵先生开会都用上海话,我们这些演员不得不硬着头皮学。"提起邵逸夫,除了电影就是大楼。
作为曾经的亚洲娱乐之王,邵逸夫拍了一千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奠基人;他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包括“四大天王”和一代代“港姐”。
同时,他捐赠的逸夫楼全国各地超过6000座。可以说,邵逸夫不是香港最有钱的,但绝对是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之一。
1957年,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请他去香港,一起搞起了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专拍华语片。
1967年,邵逸夫和朋友一起搞了个香港电视广播公司(TVB),免费播电视,硬刚当时香港电视的老大亚视。TVB出了多少男神!TVB的培训班出了周润发、周星驰、“无线五虎”、四大天王……
21世纪初有人说,香港百分之九十的明星,都是TVB出来的!
除了办培训班,邵逸夫还搞了个“港姐”选美,赵雅芝、李嘉欣、张曼玉、邱淑贞这些女神,都是通过“港姐”走红的,成了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邵逸夫于2014去世,活了107岁。有个网友总结得挺逗:“人走了,楼还在。”(许老板则是:人还在,楼不在)
邵逸夫的一生,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润,不是离开,而是带着根移植到更肥沃的土壤上。
陈光甫:
金融大佬,中国的摩根
如果说邵逸夫是娱乐圈的传奇,那陈光甫就是金融界的神话。
他创办了民国最成功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誉为“中国的摩根”。1915年,他联合庄得之等人集资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被推举为总经理。1918年,陈光甫拨款50万元设立国外汇兑处,专营外汇业务,首开中国民营银行问鼎国际外汇市场的先例。
民国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浙江兴业银行,被称为中国的“南三行”。这三家银行都立足上海,堪称中国新式银行现代化的先驱。
1949年前后,在国共双方进行生死角逐的关键时刻,陈光甫也自然成为积极争取的对象。当时,毛曾托人送来亲笔签名《毛选》一套,陈则回赠以清人书法册页。周也曾委托黄炎培请他回国,他也没有从命。
陈光甫身为银行企业家,长期接受西式教育,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可行,并且提出“提倡鼓励保护投资、全境航运开放、各省自治、裁军等”十二条建议,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49年,他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曼谷参加会议,随后定居香港,再也没有回头。
陈光甫用“润”的方式,把上海商业银行的香港分支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并在香港注册,彻底扎根。
陈光甫于1976年卒于台北,享年96岁。他用行动证明,上海人不是逃避,而是选择一片更适合生长的土壤。
陈光甫和胡适之
荣氏家族:
分散投资,资本的全球迁徙
荣氏家族的故事就是很简单了,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笼子里”的传统智慧。
荣氏家族,在解放前夕果断分头行动,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南下香港,一个远赴巴西。这种“分散风险”的决策,堪称经典的资本战略。
荣尔仁,是荣智健的二伯父,在美国做生意。1949年前夕,他去了香港;走的时候和族人约好:“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回来。” 他初期回过祖国,1951年又申请出国,先去了香港,后来去了美国。
荣鸿元,是荣宗敬的大儿子,他们那一支的头儿。他继承了他爸爸那种不屈不挠、努力创业的精神,克服了很多困难,领导着家族企业,成了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掌舵人。1949年前夕,他把工厂搬到了香港,在香港开了大元纱厂,后来又去了巴西,做面粉生意,生意很红火。
荣鸿庆,以前在申一当协理,是荣宗敬的三儿子。解放前夕去了香港搞纺织和房地产。
荣毅仁就不提了。荣氏家族的故事不仅是资本迁徙的经典案例,更是上海人应对时代变局的生存哲学。他们的分头行动,既是风险管理,也是对未来的多元押注。
演员的嗅觉:胡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蝶是中国的“电影皇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的美貌与演技,定格在无数胶片之中,是那个时代上海滩最耀目的光华。
1949年,胡蝶这位习惯了镁光灯和鲜花的影后,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嗅觉”与“执行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
她没有留下豪言壮语,没有发表政治声明,只是像一个敏感的艺术家,闻到了某种不适合她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气息。那种气息,也许是对文艺界即将到来的统一思想和政治要求的预感。
事实证明了她的嗅觉何等精准!
她那些选择留在上海的闺蜜们,如言慧珠、上官云珠等,虽然在初期也曾迎来短暂的“春天”,但最终都没能逃脱随后历次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在文哥中,遭受非人待遇,凄惨离世。
而胡蝶,虽然在香港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最终移民(专题)加拿大(专题),得以善终,成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幸运儿。
她的“嗅觉”,是艺术家对即将失去的自由与尊严的本能感知;而她的“执行力”,则是告别辉煌、决然转身的勇气。二者兼具,使她躲过了致命的风暴。
学生的嗅觉:李政道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于1946年赴美留学,虽在50年代曾短暂回国探亲,但最终选择留在美国,继续其在物理学最前沿的探索,并于1957年与杨振宁一同获得诺奖。
1951年,巫宁坤听从号召,终止了在芝加哥(专题)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学业,准备回国担任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临行前,巫宁坤在与室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后,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
年仅25岁的李政道回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李政道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可能“复杂氛围”的科研环境。虽然东瀛也重视科学建设,但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科学研究很难不受到政治的干预和方向的指定。对于李政道这样志在科学最高峰的学者而言,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自由探索、不受政治束缚、能够与国际同行充分交流的环境。
他闻到了哪里的空气更纯净,更有利于他攀登科学的顶峰。他用自己的选择表明,对于一个顶尖科学家而言,最有利于科学自身发展的环境才是关键。
李政道的“嗅觉”所指引的道路,确实让他得以在更自由的学术土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黑帮的嗅觉:杜月笙
上世纪50年代,昔日的上海滩大佬-黄金荣,边扫大街边感叹:“五大亨没义气,居然抛下我一个人扫大街!”
五大亨的代表就是杜月笙,他是旧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地下皇帝,靠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圆滑的处世哲学和冷酷的黑帮手段,构建起庞大的势力网络。他与国民党政要、金融巨头、甚至青帮分子都有着复杂的联系。
1949年,他拒绝了留在上海“合作”的建议,选择了前往香港。
他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你的游戏规则已经失效”的味道。
杜月笙深知,他赖以生存的那个旧世界即将被连根拔起。新政权带来了新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它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其体系之外的。他或许听过新政权“既往不咎”的宣传,但他更相信自己对权力本质和时代变迁的判断。
他知道,自己在旧上海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光鲜的慈善家身份,还是阴暗的黑帮头子角色,都是必须被清算的罪恶。
他闻到了空气中那股彻底清洗、不留死角的味道。他没有留下等待被“改造”或“利用”的机会,而是选择了放弃一切,远走他乡。杜月笙这份嗅觉,是旧世界“玩家”对新时代规则的清醒认知。
作家的嗅觉:张爱玲
张爱玲,一个早慧而世故的文学天才。她的文字,总游走于人性的幽暗角落与日常生活的琐碎真实之间,清醒而冷冽。1952年,她以“继续从事写作”为由,从上海迁居香港。随后,又去了美国。
张爱玲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不允许苟存”、那种不允许存在“中间状态”的味道——一种要求所有人放弃真我、带上面具、用统一的调子说话的不真实。这种味道,对一个以挖掘人性真实为使命的作家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毒气。
她笔下那些苍凉的个人故事,那些小市民的悲欢离合,那种“低到尘埃里”的私人感受,在即将到来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它们将变得多么不合时宜,甚至可能被视为腐朽落后的象征。
张爱玲的嗅觉告诉她,这片土壤即将变得容不下她这样的“异类”,她的文字将失去生存的空间,她的灵魂将被要求穿上统一的制服。
她没有留下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只是用最符合她风格的方式——悄然转身,以肉身的撤离,对抗即将到来的精神规训。
那些选择留下、经历思想改造甚至批判的同行们,他们的笔是否还属于自己。这份对比,正是关于张爱玲“嗅觉”最好的注脚。
才女的嗅觉:潘柳黛
上海滩“四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许名声不如张爱玲和苏青,但她以豁达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笔著称。
她的“嗅觉”,是一种基于社会观察和独立判断的敏感。
在1950年,当许多人还抱有幻想时,她已经敏锐地嗅出了威胁,并毅然决然地“润”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继续以写作为生,证明了即使换了土壤,她的才华依然能够滋养自己。更了不起的是,这份清醒认识,贯穿了她的一生。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面对香港即将回归,潘柳黛再次展现了她的“嗅觉”与“执行力”,立即决定第二次出走,于1988年携全家三代移民澳洲,并在那里安然终老。
潘柳黛的“嗅觉”,是清醒者对环境风险的持续评估;她的“执行力”,则是为了规避风险而甘愿放弃熟悉环境、重新开始的勇气。
两次出走,两次在新天地扎根。她的故事,是“看透+执行”最小代价、最好结局的极端例子
工人的嗅觉:倪匡
倪匡1935年出生于上海,这位以《卫斯理》系列闻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经历远比他的小说更富传奇色彩。
1950年,年仅15岁的他,怀着革命热情,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他曾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甚至主动去偏僻的内蒙古开辟劳改农场,其革命热情可见一斑。
然而,亲身经历的现实,粉碎了他对革命的理想化幻想。严酷的等级森严、无休无止的思想汇报和检讨,让年轻的倪匡浇了几盆冷水。
因为养狗咬伤书记,因为冬天取暖拆废弃小桥被举报,因为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他被视为眼中钉,面临审判和关押。
在千钧一发之际,朋友的相劝让他“看透”了危局,激发出他求生的“执行力”。他雪夜骑马出逃,辗转数千里,经黑龙江、上海,最终逃往香港。
到香港时,他身无分文,但他凭借一支笔,勤奋写作,最终成为一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并非其文学成就,而是他那贯穿始终、毫不动摇的对“自由”的坚持。
他曾说渔村如果失去“自由”就会变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对渔村九七临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现“执行力”,移居美国,继续追逐自由。直到夫人思乡,他才回港陪伴,但终生再未踏足大陆。
倪匡的“嗅觉”,是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在残酷现实面前的猛醒;他的“执行力”,是从死亡边缘逃离,并在新环境中靠才华重新崛起的顽强生命力。
他从未为某地唱过一句赞歌,用自己特立独行的一生,诠释了自由的可贵,以及一个普通人如何凭借“看透”与“敢走”,改写被注定的命运。
写在最后
70多年前,那些跑得飞快的上海人,用嗅觉和行动,将海派文化从黄浦江畔搬到了维多利亚港。他们不是“逃亡者”,而是“拓荒者”,用智慧、生意和文化,重新定义了香港的气质。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会发现,所谓“润学”并非一种消极的离开,而是主动的选择。它是一种对未来的押注,是一种基于嗅觉的生存哲学。
这种哲学,至今仍在影响着上海人(2023年),以及每一个想要从困境中突围的你我。
所以,别嘲笑那些跑得快的人,他们只是比你先一步,看清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