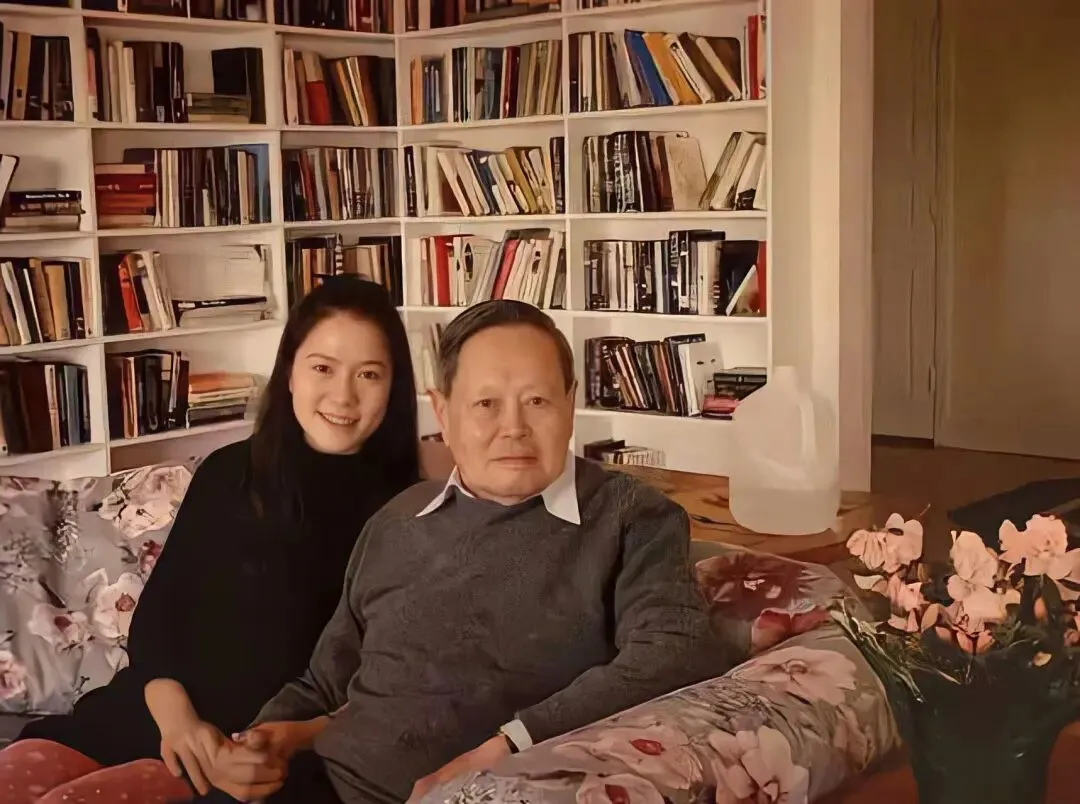100年前,科学家曾猜测今天的人类能活到1000岁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1925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58岁。
当弗雷德里克·格兰特·班廷(Frederick Grant Banting)在1921年发现了如何从动物体内分离胰岛素时,这位年轻的加拿大(专题)医生(也曾是一位一战老兵和农场男孩)彻底改变了糖尿病的死亡率。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种疾病导致超过80%的青春期前糖尿病儿童死亡。班廷的突破性发现取代了有时具有毒性的“山羊豆”(Galega officinalis)疗法。山羊豆是一类开花植物,它的叶子和花顶含有多种胍衍生物,这类衍生物具有降糖效果。班廷的发现正值医学乐观主义浪潮时期。这股浪潮由新的科学工具和知识所推动,这些工具和知识正在迅速揭开人类解剖结构、疾病和衰老的奥秘。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班廷(Frederick Grant Banting)。图片来源:Louis Schmidt - Public Domain
这种乐观主义的基础已经酝酿了几十年。19世纪80年代,人类首次发现了细菌,开启了细菌学的黄金时代,并催生出大量挽救生命的疫苗。维生素(Vitamins)得名于 20 世纪初,当时居住在伦敦的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丰克(Casimir Funk)将“vital”(必需的)和“amines”(胺类化合物)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个词。他是将常见疾病与重要营养素缺乏联系起来寻找治疗方法的科学家之一。维生素D因为佝偻病被发现,维生素C因为坏血病被发现,而维生素B与脚气病有关,这种疾病会导致患者虚弱、体重减轻、精神错乱,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致死。与此同时,麻醉将外科手术从存活率低下的可怕表演艺术,转变为在无菌手术室中更精确的程序化手术。医学似乎正在逐步征服许多对人类致命的瘟疫,从而延长了我们的平均寿命。
Free Bacteria Microbiology photo and picture
图片来源:pixabay
1925年7月,科普作家约翰·E.洛奇(John E. Lodge)甚至提出,人类的预期寿命或许很快就能延长到1000岁。“由于科学不断攻克顽疾,人类的平均寿命每年都在增加,”洛奇写道。“那么我们是否能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能够成功延长平均寿命,直到我们像《圣经》中的玛土撒拉(Methuselah)一样,以世纪而非年来衡量自己的生命?” 洛奇设想了一个可以通过更换损耗的酶、移植器官或操控难以捉摸的“生命火花(vital spark)”来延缓衰老的世界。他声称,科学家们可能即将征服死亡本身。
一百年后,我们仍未实现永生,但我们依然以同样的热情追寻着永生。如一个世纪前一样,如今这一追求并非由迷人的突破所推动——即使历史会让它们看似如此——而是通过艰苦、协作的科学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医学见解。如今,我们对基因编辑(gene-editing)、细胞重编程(cellular reprogramming)和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着迷,而不再过度关注胰岛素、疫苗和维生素。从注射干细胞让细胞永葆青春的生物黑客,到像布赖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这类依靠可穿戴技术进行预防性保健、血浆置换和热量限制的亿万富翁,战胜死亡的目标从未动摇,只是永生的灵丹妙药更加精密而复杂了。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1925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58岁,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8.4岁。与我们20世纪初的宏伟目标相比,这样的进步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一趋势表明,到下个世纪,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将达到百岁。我们甚至有理由像1925年的人们一样相信,当前许多有前景的研究,最快在未来几十年内就可能催生出新的治疗方法,显著延长我们的寿命,同时提高抵御疾病的能力。
想想新加坡的研究人员通过阻断白细胞介素-11蛋白,将小鼠的寿命延长了25%。美国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科学家成功地将一种长寿基因从裸鼹鼠体内转移到小鼠体内(裸鼹鼠的寿命比同类啮齿动物长十倍)。这种以产生高分子量透明质酸(HMW-HA)而闻名的基因,将小鼠的寿命延长了4.4%,并改善了它们的整体健康状况。研究人员的下一步目标,是将这些益处应用于人类。
不过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是,在班廷发现可以用胰岛素取代山羊豆的一个世纪后,这种粉白色开花植物的衍生物又重新受到青睐。二甲双胍(Metformin)是一种双胍类药物,已成为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主要药物之一。就像其中世纪的前身,曾被用于增加牲畜产奶量,缓解瘟疫症状,二甲双胍现在也已经被用于无数类似领域:作为抗疟药、流感治疗、催乳剂、关节炎治疗和心血管药物。如今,科学家们开始通过探究二甲双胍在细胞水平上的作用机制来解开其多功能性的奥秘。最近的研究表明,它可以减缓或抑制细胞变化从而延长寿命,而细胞变化往往会导致炎症和与年龄相关的疾病。
Free mitosis meiosis cell illustration
图片来源:pixabay
细胞衰老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科学家们发现细菌、开发疫苗、揭示维生素与常见疾病之间的联系,以及改进外科手术时,演化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提出理论,认为人类细胞具有复制极限,这解释了为什么愈合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到了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证明了魏斯曼是正确的。今天,研究人员正在研究通过重编程来阻止和逆转细胞衰老。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就尝试过这一想法,并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推进。山中伸弥发现了如何将成熟的、特化的细胞恢复到胚胎状态或多能状态,使它们能够再生为新的组织,如肝细胞或牙齿等。
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图片来源:Public Domain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寿命即将达到千岁。大多数长寿干预措施仅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或短寿命动物身上有效。将它们应用于人类将面临截然不同且极其复杂的挑战。即使我们设法将人类寿命延长一倍或两倍,同样复杂的社会挑战也将随之而来:谁将能够获得延长寿命的治疗权?我们如何支撑一个大多数人活到三四百岁的社会?如此极端的寿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心理代价?
1925年的乐观主义并非是错误判断,只是为时过早了,现在或许依然如此。但如今长寿领域的研究人员拥有更先进的工具,对生物过程更深刻的理解。现今的工具和知识能否最终让我们战胜死亡,仍有待观察。然而,如果说能从过去一百年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延长寿命是一个渐进的、脆弱的过程,而且令人觉得谦卑。我们已经将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了几十年,让曾经致命的疾病变得可控,并显著提高了人类晚年的生活质量。这可绝非易事,但仍旧并非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