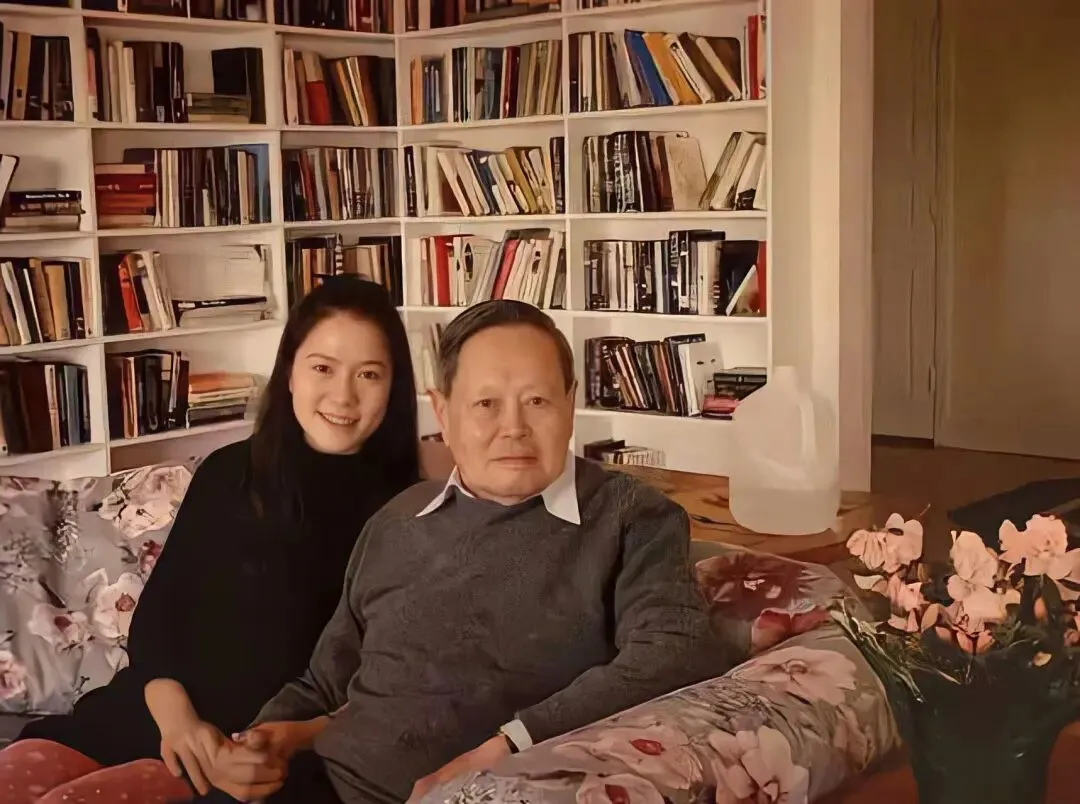美国企业为什么向特朗普“屈膝”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川普总统 最新动态!周二晚,吉米·坎摩尔重返荧屏,许多担心政府高压政治的美国人似乎松了一口气。
尽管坎摩尔的雇主迪士尼根本不该屈服于压力让这位脱口秀主持人停播——这是舆论的普遍看法,尽管商界领袖对总统霸凌行为的反抗来得太晚——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但美国企业界终归还是表明了立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写道:“这关乎为言论自由而战,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这些滥权行为。”
若以特朗普执政前八个月的情形为参照,迪士尼最初的屈服似乎更能体现这一事件的本质。毕竟,这绝非美国商界首次向白宫低头。
当特朗普首次发布行政令打击某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时,该所立即提起诉讼,另有数家律所商讨联合应对。但到了次月,这九家大律所与白宫达成了协议。
当特朗普暗示可能解雇美联储主席时,一些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还曾温和地提出反对,强调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但在特朗普真的着手解雇一名美联储理事时,这些高管却神秘地沉默起来。(特朗普声称该理事涉及房贷欺诈,但她予以否认。)
即便是与美国广播公司(ABC)同属电视媒体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特朗普因一段看似寻常的新闻采访剪辑而发起诉讼索赔100亿美元(后来增加至200亿美元)后,一度展现出抗争的姿态。5月4日,《60分钟》的记者们毫无畏惧,还采访了一名民主党选举律师,他将总统比作一个索取“保护费”的“黑帮老大”。但两个月后,CBS的母公司还是选择了和解。
为何来自媒体、法律和金融领域的领袖人物,未能更有力地反抗许多业内人士所称的总统权力滥用?
恐惧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他们害怕如若反抗会招致总统更猛烈的报复,甚至担心自己成为被针对的目标。
“那些宇宙主宰者和手眼通天的大富豪竟然如此懦弱,真是令人震惊,”曾担任企业律师和参议员幕僚,现为金融改革组织“更好的市场”负责人的丹尼斯·凯勒赫说道。“如果他们在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上都能如此卑躬屈膝,那么很明显,他们不会为任何事情挺身而出。”
纯粹的恐惧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似乎还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抗拒政府胁迫往往需要集体行动:如果企业能团结一致,而非单打独斗,它们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逐个对付单个企业很容易,”密歇根大学研究大企业的社会学家马克·米兹鲁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但如果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抗你,你就无法得逞——他会拖垮整个经济。”
然而,在过去的几代人里,美国商界精英的文化和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紧密团结的精英圈子已经瓦解,使得集体行动变得更加罕见,也更难实现。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残酷。首席执行官们往往更关心公司的股价,而非其长远的健康发展,更遑论那种模糊的、出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感。曾经把企业领袖们联结在一起的公民组织已被掏空,甚至彻底消失。
“在1950、60年代,发生这样的情况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著有《美国企业精英的分裂》(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一书的米兹鲁奇补充道。但如今,“每个人都是自顾自的。”
股东资本主义的崛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业世界是一个排外封闭、近亲繁殖的圈子,它的极致体现便是董事会——尤其是银行的董事会。为了掌握经济动向,美国各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囊括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总裁。当这些高管们围坐在会议桌旁时,他们倾向于在所有大小事务上达成一致。
正如米兹鲁奇在书中写道,这些银行董事会“通过帮助塑造相似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顶尖企业领袖群体中的规范共识与稳定性”。
这些企业高管们所拟定的议程往往远超各自公司的范围:在国内推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海外反对共产主义,而最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秩序。那是一种带有贵族气质的公共精神议程,建立在超越党派界限的共同利益感之上。他们通过各种组织和协会来推动这些议程,这使他们能够以一个统一的阵线采取行动。
华尔街律师约翰·麦克洛伊曾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以及福特基金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被称为“商界统治集团的主席”。
其他商界领袖也加入了像经济发展委员会这样的团体,倡导他们认为合理的经济政策。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通用电气的总裁、可口可乐的董事长,在马歇尔计划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敦促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来抑制失业。上世纪70年代初,当尼克松总统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低利率后,另一个顶级高管组成的商业理事会就宣布,其大多数经济顾问“强烈担忧”政府的方法会引发“更快速的通货膨胀”。(事实证明,通胀随后果然急剧恶化。)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秩序开始瓦解。全球竞争和通货膨胀侵蚀了让董事会成员感到财务宽裕的利润,社会变革也冲击了长期将董事会局限为白人男性的种族和性别壁垒。与此同时,像最高法院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这样的保守派知名人物,敦促商界领袖资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和对自由企业构成其他威胁的行动。他们的努力为航空、媒体、电信和金融等行业放松管制铺平了道路。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种新理论从象牙塔中传出。基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切斯特大学的迈克尔·詹森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该理论认为股东利益应当在公司决策中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资本主义的核心挑战是如何确保受雇的管理层(也就是高管们)做出对股东最有利的事情。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主张通过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将高管薪酬与公司股价挂钩。但他们的思路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股价表现不佳的公司成了企业掠夺者的目标,这些掠夺者会收购企业、解雇管理层,并释放出大量财富。
在十年之内,首席执行官们的激励措施已经彻底改变。在约翰·麦克洛伊和银行董事会的黄金年代,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只有一个模糊的使命去关照他们的“利益相关者”,他们追求的往往是地位和影响力的最大化。到了80年代,首席执行官们不得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最大化公司股价上,否则就会发现自己在业内混不下去。
在整个20世纪,美国顶级大企业的更替率一直很低,到了80年代,近三分之一的财富500强公司消失了,其中许多是因为恶意收购。根据米兹鲁奇书中的记载,财富500强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从1980年代初的大约九年半下降到2002年的七年左右,并一直徘徊在这一水平。
但是瓦解美国商界统治集团至少带来一个重大弊端:企业间越来越难以团结协作。高管们不再试图融入那个俱乐部,反而倾向于对俱乐部同伴下绊子。
一个明显的衡量标准就是他们在华盛顿的行为。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企业的游说还是集体行动——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而不是各自单独雇佣说客。但到了一代人之后,这种情况完全颠倒了。政治学者李·德鲁特曼的研究显示,1998年,一个典型行业大约有63%的游说经费花在了雇佣自己的说客上,而不是行业协会;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已跃升至71%。
“股东资本主义给季度盈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德鲁特曼在采访中说。而这种压力又转化为通过政府获取竞争优势的压力。“这简直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军备竞赛。”
各谋其利
在某些方面,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恰恰是在这个时刻,出现了一个决心迫使它们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总统。
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拥有数万亿美元的资产。但尽管银行家曾处于那个俱乐部的核心位置,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却一直在与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以及行为类似银行的保险公司进行着令人不安的竞争。
两位因话题敏感要求匿名的银行业官员强调,来自金融科技公司和加密货币的挑战正在上升,已引发客户可能绕过传统银行的担忧。
“如果我是传统投行,我的第一反应是:加密货币应该像其他东西一样受到监管,”《美国的生意就是游说》(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Lobbying)一书的作者德鲁特曼说。“但既然监管不可能到位,我的第二反应就是:‘我该怎么让它为我所用?’”当集体解决方案行不通时,至少要确保自己能捞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