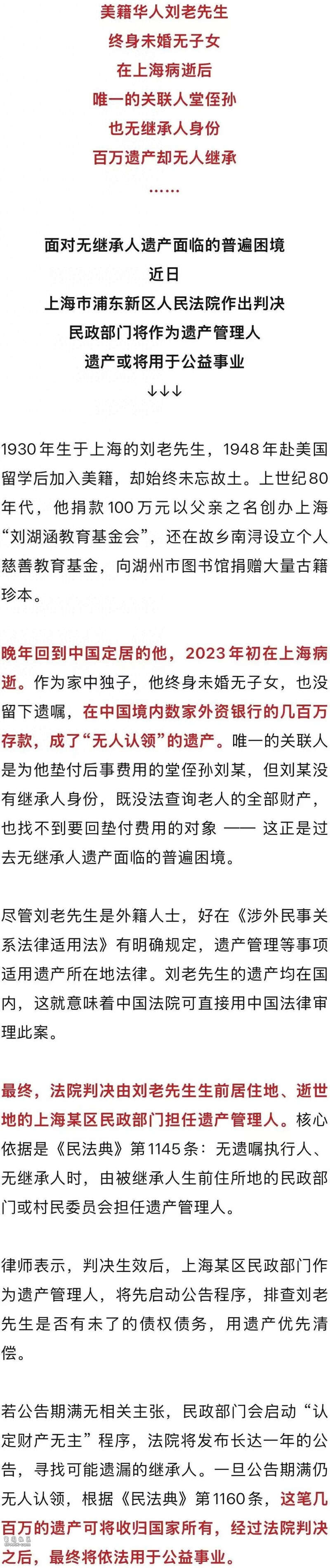中国Z世代如何把ADHD(多动症)用作了流行社交标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已经工作三年的王宁逐渐感受到“压力上涌”——她盯着电脑屏幕做报表的思绪越来越难以集中,站在打印机前,她会突然看到垃圾桶里丢弃的文件,然后忘记自己本来要印刷哪一份材料。
今年3月前,她以为这只是压力过大导致的精神恍惚,直到她有一天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博主在介绍“ADHD”这个名字——影片博主本人早已在海外医院确诊,但对于当时的王宁来说,这还是很新鲜的一种精神类疾病。
博主本人在影片里表现得非常活跃可爱,在社交媒体上广受好评,王宁在这个影片里感受到了那个和自己朝夕相伴且常常给自己带来困扰的思维模式,一切指向ADHD的临床表现:思维跳跃,不连贯,难以集中,多个声音抢夺大脑指挥权,多线程并线共行。
“看到毛绒地毯,想起小猫的毛发,于是想到了虐猫事件,然后我开始哭,”王宁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直到我开始刷到一些ADHD相关的帖子,我才知道我不是一个怪人。”
ADHD全名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常见于青少年,年幼时即可通过医疗手段确诊并加以矫正。任何心理障碍、疾病都是正常心理波动范围外的极端状态,对生活造成影响了才被称为“极端”或障碍。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ADHD作为一种影响工作效率的心理障碍,在追求高效的中国社会里本该被规避,但相反,中国Z世代年轻人热衷于自我曝光为ADHD。
中国对精神类疾病科普的缺乏导致污名化现象严重,间接导致一些精神障碍的确诊率并不高,ADHD也是其中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行病学调查数据,ADHD的平均患病率在2.8%左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推算称,中国至少有2520万人被ADHD影响生活——但确诊率低,知名度相对低,导致民众普遍对这个精神障碍并不熟悉。
澳大利亚健康专业监管局(AHPRA)注册心理学家杨欣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指出,ADHD的特征是执行功能的障碍,这可能影响需要组织、优先排序、集中注意力、调节情绪、管理冲动(选择最符合情境的行动而非随机反应)以及记忆和处理大量信息的日常任务。
ADHD虽然是一个只会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逻辑的一种心理障碍,但在追求高效、高分数的中国社会,这几乎是一个写上简历就意味着失业的瑕疵。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下,它出人意料地成为了Z世代之间流行的标签,离开了病理化的阐述背景,成为躺平、摸鱼、反对内卷、追求独立个性自我的一个连锁词汇。
走红的新名词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ADHD被很多年轻人看作一种时髦的心理障碍标签。
就像王宁所刷到的社交媒体影片一样,一些博主开始自发科普ADHD,从临床表现到用药都有详细介绍——这种详细的科普很快转化成为新的网络热词。在小红书上,ADHD直接相关的帖子有两百多万条,相关联的帖子还包括“ADHD自救”,“ADHD症状”,“ADHD调整”等,分别都有数十万条帖。
ADHD和在中国才流行起来的MBTI16型人格测试类似——这是一种心理分类分析法,在过去几年里,从韩国到中国,很多Z世代年轻人都在用四个字母排序来介绍自己,恨不得印在身份证上。“ADHD”这个心理障碍被抽象简化为一个名词,在众多社媒博主的影响下跻身其中,成为了一个流行的自我介绍词汇。
“我叫王宁,是一个enfp(MBTI分类中的一种人格类型,代表着外向E、直觉N、情感F、感知P的特质),”王宁说,自从她知道ADHD之后,她逐渐开始直接这样介绍自己,觉得这样可以更快让陌生人了解自己。
“大家都知道enfp是什么样子,ADHD现在也很火,大家也知道,这样如果我再前后无逻辑发言,或者突然神游,大家就知道这是因为ADHD而不是我没有社交礼仪。”
由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ADHD形象往往和一些活泼且人气很高的生活类博主深度绑定,谈及ADHD,中国民众的普遍印象是:思维活跃,“很有活人感”——这反过来也是ADHD快速走红中国互联网的原因,它显得无害、甚至有点可爱,无伤大雅地增添了很多快乐气息。
和ADHD一起绑定的还有迅速蹿红的辅助注意力集中玩具。
这些玩具大多是通过占用买家手部动作,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强制实现注意力集中。这些购买链接动辄有上千单交易,玩具的价格也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
到底什么是ADHD?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研究表明,智能手机等屏幕使用时间与注意力缺陷之间亦存在相关性。
杨欣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ADHD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类别,即便是没有诊断的人也有可能体验到ADHD的症状——在新冠疫情后,多项研究表明,缺乏专注力这样的ADHD临床表现在大众里变得更为普遍。研究还表明,智能手机等屏幕使用时间与注意力缺陷之间亦存在相关性。
ADHD有三个主要类别:分别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多动或者过度活跃、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体。
在澳洲,ADHD是“神经构成多样性运动”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大脑结构生而不同——在幼儿教育上,认识ADHD是一种必要的因材施教手段。澳洲积累了300多项临床心理障碍诊断,ADHD受到了关注。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在澳洲,ADHD的筛查确诊是多元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文无关)
确诊的意义
杨欣指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关ADHD的讨论,很好反映出社会对于心理健康认知的提升。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澳洲也就是广义上的国外用的是两套系统,中国的系统里是没有ADHD这个东西的,这个词能走红,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民众不愿意再去服从集体主义,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强调思维多元的ADHD就成为了这个趋势下最显学的存在。”杨欣这样说。
王宁来自一个中国中部的县城高中,这个学校亦曾效仿疯狂追求高考成绩的衡水中学模式。王宁高三那一年,校方给每一个教室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并在学校门口放置了巨大显示屏,邀请学生家长随时来监督自己家或者别人家小孩的在校情况。第几排第几座在课间休息时间吃零食这样的事情如果被监控室的保安、或者某一个学生家长目击的话,这个学生会被广播全校通报批评。
这个巨大的监控直播设置在县城里收获了普遍好评——学生的成绩确实有提高,尽管关联因素并不可追溯。
走出校园后,她进入一家国企,虽然没有大厂那般过度加班,形式化的活动只多不少,她一度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才26岁,过模版人生,行将就木。
王宁说,那几个博主的影片唤醒了她的一些记忆——ADHD被当作一个出口,承载了很多中国Z世代年轻人无处抒发的浪漫幻想。在小红书上,一些用户亲切地称呼ADHD为“小猫在草丛里追蝴蝶般的思维模式”。在追求就业率、追求正确、追求复制和进步的中国职场环境里,坦白说“我有ADHD”和坦白“我可能没那么好管理”直接画上等号
中国民众将ADHD的语境几乎仅限定在工作场合。“在家休息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去考虑做完A是不是要立刻做B以提高效率,只有职场是这样。”王宁说。
她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完了检查并完成确诊、拿到了帮她提高专注力的药物,并不停问医生ADHD是否会“留档”——在中国,精神分裂、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疾病被要求留档管理,抑郁等疾病亦有一定概率进入个人档案,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影响本人就业等社会活动。
王宁说,尽管她吃药后不久,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有加快心率一条,她感到身体不适于是立即停药,在确诊单到手的时候她还是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她的跳跃性思维并不是她的错,而是“大脑生而不同”。
杨欣亦肯定诊断本身对于ADHD群体的作用。
“对于个人而言,这种广泛讨论本可以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缺失拼图,或者一种解脱感——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自我确诊可以让他们把生活里的一些挑战解释为大脑的自然变化,而不是‘这是我的错’、或者‘我没有努力足够多’,”杨欣说,“还能帮助他们形成一个社群,更有利于去构建一个包容和有同理心的社会。”
去儿科门诊看病和拿药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传统印象中,“多动症”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
此外,杨欣指出,ADHD这个概念的快速走红,也意味着中国民众过于迫切寻找一个“全合一”的生活万能解释——这有一定概率是在掩盖他们生活里真正的问题。
“ADHD始终是一个西方式的概念,是在西方定义框架下的诊疗,它能多大程度适配中国体系下的个体经验?这里要画一个问号,种种心理障碍都不是一个原因所导致的,它们都是综合作用的产物,”杨欣说,“而且,对于所有的心理诊疗来说,诊断本身只是第一步,并不是终点……你有ADHD,然后呢?”
一些中国民众很自然的下一步跟王宁一样:吃药。
李女士供职于上海的一家律所,长时间的案头工作并不允许她有太多时间付诸个人情感或杂乱思绪,效率是她留在这里的唯一依凭。在前往医院确诊之前,她已经知道了自己“十有八九就是ADHD”,而且她很清楚,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矫正ADHD几乎不可能:她是一个律师,没有时间这样做。她需要最直接的药物。
针对ADHD的精神类药物在中国受到严格管控的,需要通过医院门诊才能获得——但是,由于中国成人ADHD诊断启动过晚,能给成年人进行诊断的门诊数量非常有限,像李女士这样有明确开药需求的人就会陷入困境:什么时候才能请到假、挂到号。犹豫再三,李女士最终是在儿童精神科完成了确诊和拿药。
在请假去开药之前,她先依照小红书的提示给自己购入了一个ADHD辅助专注玩具:一个莫比乌斯环形的塑料捏捏。仅在她下单的那一家网店里,这一件产品即已售出6万单。
李女士坦言自己很担心没有帮她完成专注的药物的话,情况要怎么办。
“我没有时间去系统性地处理我的问题,我需要长期专注,我知道专注不了不是我的错,但我是个律师,我需要专注,”李女士焦虑地表示,“今天我可以靠买这些捏捏缓解,明天要怎么办?我怎么会工作到没有时间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