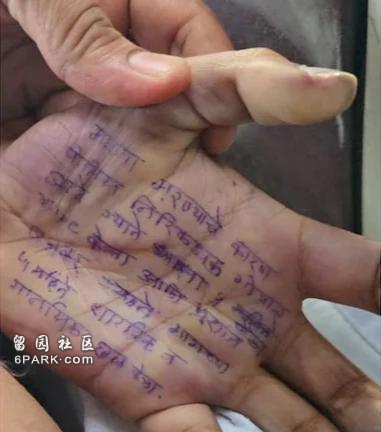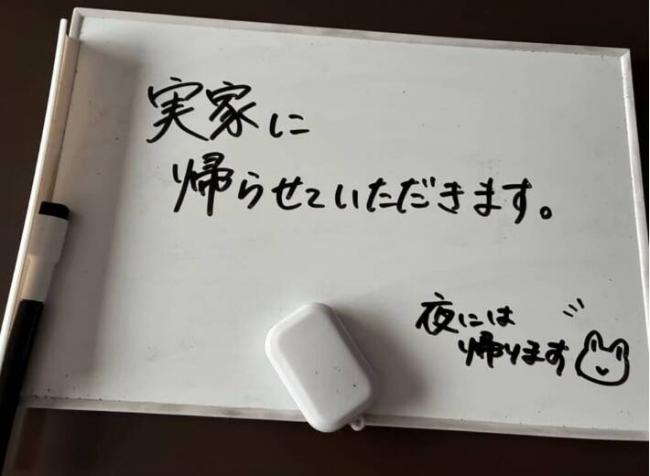乐观的大脑是相似的 悲观的大脑各有不同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无法预知的未来往往引人遐想,但是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想象未来的方式非常不同。在乐观的人看来,前途是光明的,好事会很快到来,而在悲观的人眼里,不仅将来的结果是黯淡的,过程也不会顺心。因此,一些人总喜欢推崇乐观,贬低悲观,奉劝他人转变思路再积极乐观一点。然而,乐观和悲观并不是主观意识层面想开点就能立刻轻易扭转的。神经模式的差异最近,一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通过对大脑影像数据的分析表明,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在思考未来情景时,大脑的神经表征具有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在更乐观的人的大脑特定区域,神经模式具有相似性,而偏悲观的人在这方面却各有不同。

研究人员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获取参与者的大脑数据,他们所关注的大脑区域主要是内侧前额叶皮层。视觉中国|图
这些大脑数据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获取的,在多个试验中,研究人员分别安排参与者思考一些关于未来的情景,同时对他们的大脑影像进行扫描,随后结合这些人的乐观程度,对他们的大脑数据进行分析。相关研究2025年7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所关注的大脑区域主要是内侧前额叶皮层。
“我们在内侧前额叶皮层观察到的共同的神经模式,反映了乐观的人们想象未来的一种共通的方式。”开展这项研究的神户大学副教授柳泽邦昭(Kuniaki Yanagisaw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内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自我参照及基于价值的思考,所以,这些神经层面的相似性很可能代表着人们在构想积极未来事件时,共享着特定的认知情感风格。”
在试验中,参与者实际上被引导构想了一系列未来的场景,比如一些偏积极的事件,包括将要进行一个环球旅行的壮举,或者在比赛中大获全胜等,一些偏消极的事件,如将要被公司裁员甚至诊断出癌症晚期等,以及一些偏中性的事件。而且这些未来事件的假定主语不仅包括参与者本人,还包括他们的伴侣。由此,参与者以自我为参照,通过想象的方式,默默地输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将相关的大脑活动真相留在了测量仪器中。
关于乐观与悲观的认定,经典的测量方式主要关注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如果一个人在不确定的时候,通常都期待着得到最好的结果,觉得自己身上将要发生的好事肯定多过不好的,对自己的未来总是持乐观的态度,那么这个人的乐观程度就比较高。相反,如果一个人总觉得自己身上几乎不会有好事发生,总会出点什么问题,事情不可能如己所愿,那么相应的乐观程度就比较低。
乐观者并非好坏不分而且这种乐观程度的差异,并不只是影响人们生活的心境。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乐观程度也会影响人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更乐观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也会有更好的社交关系网,不仅朋友多,对关系的满意度高,也能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而最新研究的发现意味着,乐观者的社交关系优势背后,共享的认知结构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研究人员分析,乐观者在社交圈中比悲观的人更受同伴喜欢,更具吸引力,这不仅是受到乐观人格特征的影响,也可能因为这些人之间本身就有共同的认知结构。因为有神经影像研究表明,在一个社交网络中,那些占据中心位置的人,他们的神经反应跟这个社交圈中的同伴是很像的,特别是在一些涉及观点和主观理解方面。乐观的人们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相似的认知结构彼此组成了更大的社交网络,而不那么乐观的人之间,因为彼此的认知结构差异更大,各具特点,致使自身社交连接受限。
在日常生活中,一般而言,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乐观者相比悲观者的这种优势,主要在于乐观的人能够笑对一切,甚至苦中作乐,不论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积极事件,还是消极事件,他们都能等量齐观,宠辱不惊,乐观相待,但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研究发现,乐观者的认知特点并非如此。

乐观者在社交圈中比悲观的人更受同伴喜欢,更具吸引力。视觉中国|图
与刻意模糊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心理边界截然相反的是,数据表明,乐观的人恰恰是在大脑中把积极的事件和消极的事件分得很开,相比悲观的人,他们在想象未来的时候,会放大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之间的心理差距,明显将积极事件作为优先项考虑。
研究人员认为,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所谓乐观,并不是对负面事件重新解释,强行积极乐观,而是将这些负面消极的未来事件以更抽象、心理距离更远的方式加以处理,对于积极正面的未来事件,则把它们想象得更生动、更具体,以此强化积极事件的情感影响,缓解消极事件对情感的冲击。不过,无论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这种神经特征虽不能轻易反转,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重要的是,这些神经模式是由经验、学习和社会环境所塑造的。乐观并非注定不变——它会随着我们的思维框架和生活经历的改变而增强或减弱。”柳泽邦昭解释,尽管如此,最新研究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努力变得更乐观,或者一定要在内侧前额叶皮层形成相似的神经活动模式。
他介绍,虽然乐观在许多情况下对心理幸福感有益,但也并不是普遍如此,在一些情况下,务实的谨慎,甚至适度的悲观,反而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挑战。“我们的研究发现所真正强调的,恰恰是人们想象未来方式的多样性。理解这种多样性,而非推崇单一标准,才能帮助我们真正领会人类适应生活,并寻找生命意义的不同之道。”
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这种与乐观和悲观有关的生存之道,甚至并非人类所独有。2025年6月,明斯特大学神经与行为生物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生物学评论》发表研究指出,乐观与悲观,不只与人类有关,或许也是人们理解行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对整个自然界的物种而言,它们同样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去预判结果的好坏,由此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乐观的动物会倾向于预判得到更有利的结果,而悲观的动物则会把结果想得更糟糕。
以老鼠为例,当一只老鼠听到附近的灌木丛中有声响时,这种不明来源的环境因素就需要老鼠对自己的境况做出解读和回应。悲观的预判可能会认为这是天敌的声响,相应的行为应该是逃跑和躲藏,而乐观的预判可能会认为这只是风吹树叶的自然声音,相应的行为自然是不必理会,继续待着觅食。研究人员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老鼠实际上面对着不对称的成本和收益。
如果周围没有危险却跑了,这相当于无端耗费了不必要的能量,但是如果有天敌却不跑,面对的就是致命的威胁。在这些环境下,悲观耗费能量,乐观损耗生命,不对称的成本和收益会促使生命体倾向于朝着悲观的方向寻求适应,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想法。但反过来,如果是没有天敌的环境,更乐观的应对方式显然更能适应。可见,乐观的大脑是相似的,在自然界,一样与生命体所处的环境相适应。
“有多项针对人类乐观与悲观特质的研究表明,乐观者与悲观者应对环境影响的方式存在差异。”参与这项生物学研究的维多利亚·西韦特(Viktoria Siewert)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动物群体中可能同样如此,“因此,我们的研究发现,或许对生物多样性与物种保护等更广泛的领域也具有启示意义。”
在她看来,环境变化无处不在,而在当今世界,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快速变化尤为剧烈。动物必须有效适应这种多样化的环境条件才能生存。正如他们的研究所发现的,作为行为生态学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如果个体的乐观和悲观倾向与其适应能力的差异有关,那么这将深刻地影响个体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在这方面,已有基于斑马鱼的实证研究发现,乐观和悲观的认知偏向会影响多项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2025年3月,葡萄牙的研究人员通过观察斑马鱼表明,悲观和乐观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明显不同,而乐观者的压力反应程度较低,同时对疾病有更强的抵抗力,癌症的发病风险更低。相关研究发表在《转化精神病学》,研究同时还证实,斑马鱼在乐观和悲观方面的判断倾向,是一种稳定的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并不会轻易改变。
理解乐观的规律这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自然界中,既然环境不断变化,那么乐观和悲观相关的行为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重塑的。结合相关的研究,明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涉及个体应对环境的至少两种策略,一种是选择环境,一种是适应环境,而相比前者中个体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后者在被动适应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重塑自己的行为模式。相较而言,悲观者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更具有可塑性。只是这样的分析,未来仍有待更多试验来验证。
“我们一般将乐观或悲观理解为同时包含‘状态’与‘特质’两个组成部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乐观或悲观倾向可以被视为是相对稳定的。”主要研究情感和认知的维多利亚·西韦特解释,在各类动物中,尽管乐观或悲观可以从状态和特质两个方面来理解,但总体上这种倾向都是相对稳定的。虽然目前因为缺乏相关的研究,动物中乐观或悲观这一特征的遗传基础还不太清楚,不过在人类中,相关的遗传率估计在23%至30%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实验室最近一项研究所证明的,乐观或悲观特质的稳定性在生命不同阶段可能并不相同。例如在大鼠研究中发现,这些特质似乎在成年期得到巩固。”她还解释,“尽管存在这种稳定性,然而,乐观或悲观仍会受到环境影响。例如,恶劣的居住条件、疼痛,或社会剥夺等负面的经历,已被证明会增加悲观,而积极的经历,如改善的居住或社会接触,会增加乐观。”
对人类而言,已有大量科学证据表明,乐观程度会在童年早期逐渐减弱。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总结认为,这背后主要有三种发展机制。一方面,儿童随着年龄增长,会积累大量亲身经历和社会反馈,不断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会让人从乐观变得更现实。另一方面,随着儿童对社会的理解加深,也会对成功的原理和预期的界定有更清晰的认识,更能意识到努力不等于能力,天马行空的“希望”与考虑实际的“期望”也不是一回事。加上儿童年龄变大之后,也更善于从负面结果中学习,这种学习偏向同样会加速儿童变得更现实,导致乐观减少。
正如最新针对人脑的研究所展示的,进入成年期后,不论男女,这种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在大脑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记,由此做出了不同的预判,有了差异化的行为,以及不一样的社交圈。其中,乐观者的大脑彼此更为相似,悲观者的大脑则各有不同。研究者认为,这正契合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乐观的人是相似的,每个不那么乐观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着未来”。
“从根本上说,这项研究是为了理解我们对世界的内在表征,即我们的希望和期望,在个体之间是如何保持契合或错位的。我相信这样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使人们能够共享希望而非彼此孤立。”柳泽邦昭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当我们想象未来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进行个人思考,也是在与其他人共享心灵图景。乐观的人可能会看到相似的未来,而这种共同的愿景可以在社会中培养一种连接感和希望。”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责编 朱力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