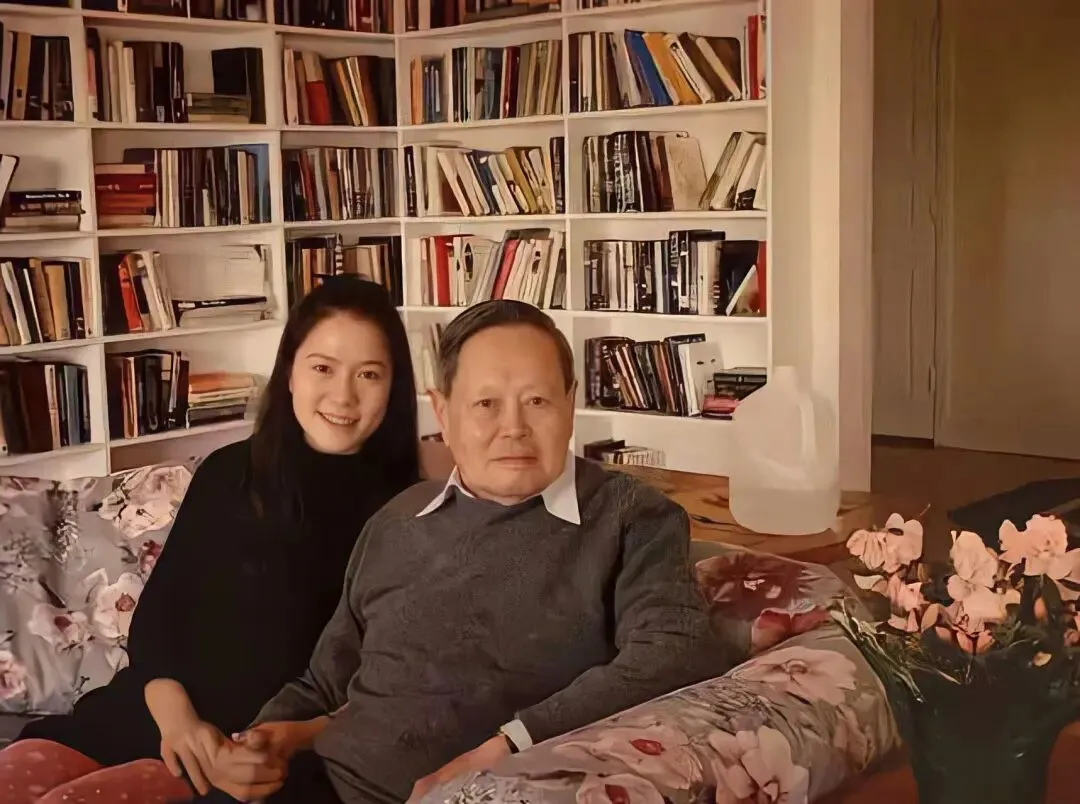美国主流媒体的自我流放 — 媒体失守,真相流亡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在美国政治史上,共和党总统与主流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新鲜。里根曾被嘲讽为“演员总统”,小布什则被批成“头脑简单的牛仔”。然而,没有哪一位总统像唐纳德·川普那样,遭遇如此密集、持续、且带有强烈敌意的媒体攻击。过去九年间,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报道几乎从未松口。这种“川普综合症”(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不仅重塑了政治叙事,也深刻改变了媒体自身的生态与信誉。
2016年大选夜,川普出乎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媒体世界在震惊中短暂地停顿了几个小时,那是一次罕见的自我反思:“我们怎么会看走眼?我们是否与美国脱节了?”然而,这段反思期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几乎不间断的敌意与否定。媒体对总统保持严厉监督是天职,但监督不等于偏见,更不等于以立场取代事实。这条职业底线,在过去的九年里,被反复冲击。
最近,两位在主流媒体工作多年的资深记者——《华盛顿邮报》前“事实核查员”格伦·凯斯勒(Glenn Kessler)与ABC新闻前资深记者特里·莫兰(Terry Moran)——离开岗位后,先后在自己的Substack平台上公开谈到媒体的立场问题。
凯斯勒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了27年,以“匹诺曹”评级系统闻名。在离开前,他曾建议报社恢复“读者申诉专员”制度,让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专门监督媒体是否公平报道。然而,他在文章中直言,《华盛顿邮报》的读者群体主要是自由派,其商业模式也依赖这些自由派读者的订阅收入。于是,一个“难题”出现了:如何在不流失核心自由派读者的情况下吸引保守派读者?凯斯勒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
他甚至坦率地承认,保守派虽然是一个潜在增长市场,但对自由派占绝对多数的《华盛顿邮报》来说,主动争取保守派读者,等于要冒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风险。换句话说,报纸无法真正做到“中立”,因为中立会伤害商业利益。这不是孤立的观点,而是主流媒体编辑部中普遍的潜台词——只是极少有人愿意公开说出来。
莫兰的表述更加直接。他在评论ABC新闻的文化时写道:“在ABC新闻或其他传统新闻网络里,几乎没有人支持唐纳德·川普。这必然会影响新闻报道。老牌新闻部门听不到全国许多人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根本不存在于新闻编辑部中。”这不仅是立场问题,更是信息源与议题选择的结构性偏差。
凯斯勒的坦白和莫兰的直言,都指向一个核心:新闻公正的危机。
新闻公正(Journalistic Fairness)并不意味着报道必须对各方平均分配篇幅或语气,而是指记者在收集、验证、呈现信息的过程中,应当尽最大努力避免让个人信仰、政治立场或商业利益影响事实的完整呈现。它的核心,是程序上的中立性和方法上的诚实。
经典的新闻伦理学认为,公正包含三个维度:
1. 信息的全面性:在同一议题中,尽可能呈现各方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刻意省略不利于某一方的事实。
2. 事实的独立性:信息的来源和验证必须独立于被报道方,不能依赖单一阵营的叙事框架。
3. 立场的自觉克制:记者和编辑应当意识到自己难以完全“无立场”,但必须在报道中最大限度地削弱这种倾向,而不是将其包装成“客观真理”。
真正的新闻公正,不是站在正中间平均分配好坏,而是让事实自己站立,即便它会让某一方不舒服。正如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说:“新闻的使命,不是去安慰某个阵营,而是去照亮公众所处的世界。”
当媒体将“公正”当作营销标签而非职业信条,它就变成了选择性公正。在某些议题中严苛挑剔,在另一些议题中轻描淡写。这不仅背离了新闻的初衷,也让“公正”沦为另一种立场的外衣。
媒体偏见不仅是职业操守的缺陷,还会产生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后果。第一,这是职业失职。媒体作为民主制度的第四权,必须监督所有掌权者、为公众提供尽可能全面和准确的信息。当一个机构系统性地偏向某一方时,它就放弃了履行这一职责的资格。第二,这是政治反效果。偏见反而帮了川普。许多原本对他个人和政策都有保留的选民,正是因为厌恶媒体的立场化报道而投票支持他,用选票去惩罚这种垄断叙事。第三,这是信任侵蚀。当主流媒体被大规模视为“不可信”时,公众对制度本身的信任也会动摇,这种破坏是缓慢但致命的。
凯斯勒的承认也揭示了一个被高层讳莫如深的现实:商业模式会直接塑造新闻立场。过去,《华盛顿邮报》《纽约(专题)时报》凭借全国性影响力和多元受众,能够维持较高的编辑独立性。但在数字化冲击和订阅制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它们越来越依赖核心订阅群体的忠诚度来维持收入。如果这些核心用户是自由派,那么媒体就会倾向于生产迎合他们立场的内容,避免触犯他们的政治敏感点。这是一种“受众绑架”——新闻价值被市场逻辑吞噬,公正报道反而成了商业风险。
尤其在当下,美国社会的分裂程度空前加剧。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主流媒体做不到公正,至少应该坦诚承认自己的立场。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新闻编辑部的人不仅无法做到公正,还拒绝承认自己有偏见。看看美国的几档晚间脱口秀节目就明白了。CBS、ABC等电视网的Late Night Show,如今几乎成了政治宣传部门的延伸。过去Jay Leno主持《今夜秀》时,虽然也谈政治,但本质上还是喜剧娱乐;而今天的晚间脱口秀,政治化到几乎沦为单一阵营的扩音器。
成为左倾媒体并不可耻,左派也完全有权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问题在于,他们一边做着高度立场化的内容,一边却自称“独立”“公正”。如果ABC、CBS、NBC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民主党倾向的宣传媒体”,至少公众还能在明白真实定位的前提下去判断他们的内容。现在的状况,是他们做着党派媒体的事,却假装自己是无偏见的“中立机构”,这才是真正伤害信任的地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流媒体对“事实核查”(Fact Check)的痴迷。表面上,这是一种严谨求真的新闻态度,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它在潜意识里带着浓重的道德审判色彩,几乎像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
《华盛顿邮报》的“匹诺曹笔记”(Pinocchio Notes)就是典型。他们设计了一整套打分体系,一根鼻子表示“小小的不实”,四根鼻子就是“撒谎到极致”。形式可爱,寓意轻松,但背后传递的是一种无可置疑的裁决口吻:我对,你错。这种姿态带有与生俱来的崇高感,仿佛站在历史与真理的制高点,对政治人物乃至公众进行道德宣判。
这种“Fact Check 崇拜”本身就带着讽刺意味。你很少看到右派媒体如此系统化地经营“道德裁判所”。右派通常会直接表明立场,和你辩论观点;而左派媒体则更喜欢披上中立与科学的外衣,让一切变成“结论已经确定,只等你承认”。这在新闻传播的心理效果上,比直接的政治攻击更具杀伤力,因为它既能保持“新闻人”的体面,又能暗中完成立场塑造。
更讽刺的是,当这种核查用于自己人时,标准往往灵活得多。例如,2020年大选期间,有人质疑拜登在演讲中读错地名、逻辑混乱,事实核查的结论是:“不能据此质疑其认知状态”,理由是“任何人在长时间讲话中都可能口误”。结尾甚至附带一条“川普也曾读错地名”的注释,成功把一方的核心质疑转化成“双边口误”的小插曲。
这种自我正义感不仅停留在方法论上,还经常体现在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中:
CNN在2020年疫情期间曾做过一次“事实核查”,对象是川普说美国正在开发疫苗,并可能在年底前投入使用。CNN当时援引匿名专家的话称:“几乎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这种说法是危险的虚假承诺。”结果年底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率先获批,CNN没有为当初的判定道歉,只是默默在网页底部加了一行“更新:疫苗研发已提前完成”,像是替自己改试卷分数的老师——错了,但不承认,只是悄悄修正。
CBS的一次国际新闻报道中,委内瑞拉反对派举行抗议,标题是:“混乱爆发,安全部队与示威者冲突”,配图是街头的火焰与警察的防暴盾牌。而当同样的场景发生在美国波特兰时,标题换成了:“抗议者与警方在要求社会正义的集会中相遇”,画面换成手举标语、面带微笑的人群。语言和画面的选择,让同样的事件在观众心中留下完全相反的印象。
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披着“新闻中立”的外衣,却在叙事框架、细节选择、事实裁定上,将立场深深嵌入报道之中。对于受众而言,这种包装比赤裸裸的党派宣传更有迷惑性,因为它让人误以为自己接触到的是未经修饰的现实,而实际上,这只是经过精心导演的现实片段。
凯斯勒与莫兰的发声,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主流媒体内部久已存在的结构性偏见。遗憾的是,许多人看见了,却依然选择说“这没什么问题”。如果这种态度持续下去,美国新闻业将失去它最宝贵的资本:公众的信任。
真正的问题,是公共机构的中立性是否还值得信任。媒体早已不只是“第四权力”,而成为国家认同与价值观之争的战场。
记者也早已不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而是主动投身战场的“意识形态突击队”。问题来了:为何美国的学校、主流媒体、文化机构几乎清一色左倾?这真的是川普惹的祸,还是某种更深层的体制漂移?
乔治·奥威尔说:“在欺骗盛行的时代,说出真相就是一种革命行为。” 当真相与立场难以分辨,当新闻与宣传在同一版面共存,我们还能相信谁在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