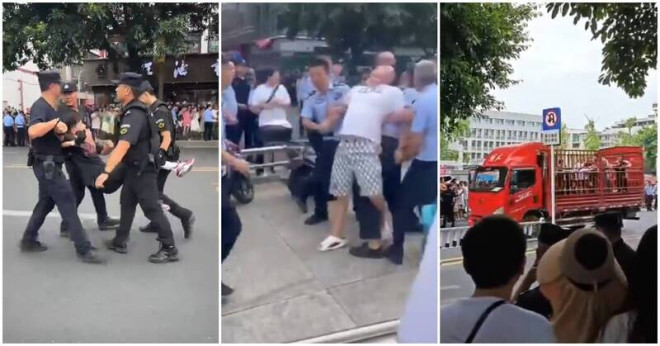在这最神秘的地方,发现了“奇迹”....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在中国数十万公里的国道中,有三条极为特殊,它们蜿蜒迤逦、彼此相连,环绕着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其中又以G219国道最为壮丽,北起新疆哈纳斯,南至广西东兴,一路途经草原、沙漠、戈壁、高原、雪山、雨林、海岸,总里程10065公里,被誉为“国之大道”。
G219国道的5000公里处,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嘎拉乡。如今,许多自驾路过的游客都会在此驻车打卡,不单因为这是一个中点,也不全因为秀美的风景,更因为这里矗立了一座别致的雕塑。那是一个铜制的卷轴,展示了西藏史前先民的渔猎生活。

G219国道的5000公里处的一座卷轴雕塑,展示了西藏史前先民在玛不错湖畔的渔猎生活。摄影/本刊记者 徐鹏远
曾经,这样的场面就鲜活地呈现在西北方向一个叫作“玛不错”的湖泊之畔,那里水草丰茂、物产充足,哺育了早期特殊环境中的人类,繁衍出一脉独特的高原文明。只是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古老的图景或在时光的流转里消逝,或在历史的尘埃中埋没,几千年来都未曾为人所知。直到过去的五年里,随着一番持续的科学发掘,当初的勃勃生机才又显露出种种痕迹与线索。
在这个意义上,这座雕塑不只是G219国道的一个里程碑,它琢刻的同时是西藏史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玛不错遗址。迄今为止,这是青藏高原腹地所发现的年代最早、海拔最高、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今年4月,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入选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而一切的开始,都要从几枚陶片的意外采撷说起。

坐落在玛不错湖畔的遗址第四期石构地面建筑考古发掘现场。图/新华
依湖而生
从G219国道拐向玛不错,直线距离不过4公里左右,真正走起来却遥远得多。它们之间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迂回崎岖的土路,实际上绕出了20多公里。
2019年,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杨晓燕就是在这样的曲折与颠簸中走到了湖边。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的她,正在进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田野调查,雅鲁藏布江支流年楚河的沿线区域是她考察的重点之一。
具体线路是夏格旺堆帮忙规划的。作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他的选择带有明确的考古意识:“年楚河流域历来是后藏地区的粮仓,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很多藏文文献里都记载着7世纪以后这里人才辈出。但是过去的工作当中,我们始终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所以也就没有发现过比吐蕃更早的遗址。”
然而开始的前几天,收获并没有期待的那么大,因此当杨晓燕一行人来到玛不错时,原本也没抱什么希望。但就在将要离开时,杨晓燕一犹豫,还是下车看了看,结果这一看就看到了惊喜。
今天的玛不错,周围是一片广袤的草原,附近牧民都会来此放牧,为了方便,他们在湖岸边两处隆起的小丘之间修了一条村道,于是明显的文化层从东南方向的阶地剖面露了出来。就是在这个剖面中,杨晓燕看到了一些陶片,她立马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夏格旺堆,随后收到回复——它们至少应该早于3000年前。
“2003年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我们在羊八井发现了加日塘遗址,确定是距今3200至2900年。照片跟加日塘的陶片特别像,我就感觉玛不错起码不会晚于加日塘。”夏格旺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陶片以及一些同时发现的骨块、炭化农作物种子等样本被送进了实验室,借由精确的测年,确定为3800至4000年前的遗物。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突破,此前4000年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只在西藏东部的考古工作中有过发现,而在中部一直处于空白。
次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一支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向玛不错迈出了发掘的脚步,夏格旺堆担任队长。经过详细勘察,湖滨的遗址范围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位于东南岸、南岸和西北岸,总面积达22.4 万余平方米。
对西藏地区而言,考古发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高海拔就足以带来重重困难。最关键的是,自然条件留给野外作业的窗口期很短,像是玛不错这样4400米以上的地方,每年只有6月到9月之间的百余天时间。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玛不错遗址发掘取得了极大收获。
特别是60余座墓葬的出土,给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些墓葬依照不同的时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比如,在距今4000至3300年的第二期,以土坑墓为主,同时存有叠葬墓,属于西藏高原墓葬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再比如,以石室墓为代表的第三期(距今3300至3000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封堆墓,将这种墓葬形式的认知记录从7世纪吐蕃时期直接提前到了史前时代。
墓葬内人骨所呈现的葬姿也非常多样,包括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二次捡骨葬等,几乎西藏其他地区能见到的丧葬习俗都存在于玛不错遗址。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段出现的俯身直肢葬,更是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一些遗址(如青海省宗日遗址)的发现相一致,而且通过人类古DNA的检测也发现,两地人群在基因上就有着密切的关联。
不仅仅是葬俗,稻、粟、黍等农作物遗存都说明了彼时的西藏中部早已与中原、西南山地、西域等地区产生交流,而遗址内发现的海贝、象牙、青铜器、玛瑙、红玉髓、费昂斯等贵重遗物则暗示着远距离贸易的存在。“我们推测,4000年前玛不错区域已与周边地区构建起广泛通畅的互动,这极大地延展了学界对‘史前全球化’时间和空间的认知,为探究史前人类文明打开了全新视角。”夏格旺堆说。
另一个饶有意义的发现则是遗址内的大量鱼骨和骨制鱼卡等捕鱼工具。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基本可以确定,鱼是当时的主要食物来源。
夏格旺堆介绍,其实玛不错南面的陆地原本也是一片湖水,最大的时候有100多平方公里:“4000年前,这里的水量很大,鱼的个头也很大。但距今3800年前之后,鱼的个头开始变小,说明这一时期湖水开始干涸。等到了3500年前左右,绵羊、山羊、黄牛这些就都出现了,包括在第四期(距今3000至2000年)的遗址堆积中,我们还发现了大量人类食用后散落的鸟蛋壳。”
不过即便如此,鱼在玛不错先民的食谱中依然没有彻底消失,因为也是在第四期的石构建筑里同时出现了石制的网坠,这意味着在鱼资源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渔网进行捕捞。

上图:玛不错第一期遗址(距今4500至4000年)墓葬中俯身直肢石棺墓和土坑墓。图/新华
下图:玛不错第一期遗址出土遗存典型骨器、石器、蚌器、滑石珠等。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供
水泥厂下的遗址
作为西藏中部发现的第一个超过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玛不错遗址不仅为构建西藏历史提供了更多材料,也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了新的类型。
就史前考古而言,文化类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通过相关特征的区分,为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遗存进行谱系化归类。通常,对文化类型的划定是以陶器为典型标志和重要依据的。
玛不错遗址出土的陶器,便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第一期没有完整的陶器,只在一些碎片上隐隐约约找到了平底器底,第二、第三期则很明显,第二期是平底和圈足,第三期是平底和圜底,完全是本地风格,而且彼此之间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夏格旺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器型区别于已发现的其他遗址,“比如卡若文化的陶器全部是平底;曲贡文化的陶器以圜底为主,有部分的圈足;玛不错恰恰是站在它们中间。”而无论卡若还是曲贡,此前都被认为是西藏无可比拟的原始文化遗址。
相较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西藏地区考古的起步要晚了许多,但卡若遗址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不仅颠覆了旧史学中的有关认识,重塑了西藏史前史,还首次将西藏史前人类的发展进程与相邻地区紧密联系,科学阐明了青藏高原并非“孤立的荒漠”。在2021年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它也成为唯一入选的西藏遗址。
1977年,当时的昌都县卡若村在扩建水泥厂时发现了一些精致的器物,有的形如石斧,有的质若玉石。正巧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厂里放映一部有关出土文物的纪录片,工人们想起刚挖出的东西似乎与银幕上的有几分相像,便联系了昌都地区文化局。又适逢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三名文物干部来征集文物,经过他们的鉴定,初步判断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卡若遗址的发现就是这么偶然,如果不是水泥厂扩建,到现在可能还埋在底下,因为它的地表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层将近两米厚的泥,这个泥是发大水冲积过来的,把早期的遗址全部覆盖了。”侯石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75岁的他当时才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援藏,有幸参加了卡若遗址1978年的试掘和1979年的正式发掘。

上图:西藏昌都市卡若遗址公园内的复原古人类生活场景。图/IC
下图:昌都市卡若遗址公园一角。图/IC
据估计,卡若遗址的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但一部分已遭破坏,残存不足5000平方米。通过两次挖掘,1800平方米的遗址得以揭露,除去500平方米空方(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总共获得7968件石制工具、366件骨制工具、2 万余片陶片、50件装饰品和几个陶纺轮。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地面石墙、石子小路、石台基等遗迹和28座房屋遗址。同时依照碳-14测定结果,遗址的绝对年代确定为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
所有遗存中,石器、陶器、半地穴房屋以及大量粟、黍和动物骨骼尤其值得关注。它们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等西北文化类型乃至营盘山等西南文化类型,显示出了诸多相似之处。正如侯石柱所说:“卡若文化很可能是从黄河上游来的一个原始文化,并在随后向四周扩散。几千年前,西藏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文明的交叉路口,一个南北向的大通道。”

上图:卡若遗址出土的赭红色陶罐(左)及小口垂腹罐。图/视觉中国
下图:2015年7月,西藏博物馆展出的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景观。图/视觉中国
包括已成为西藏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也印证着这种关联性。“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双典型纹样是蛙纹,一开始很象形,一看就是青蛙,后来发展得比较抽象,逐渐向几何形态过渡。卡若遗址的双体兽形罐上是折线纹,像是字母W的不断重叠,源头其实就是从马家窑的蛙纹演变过来的。”侯石柱说。

左图: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陶罐,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代表作。图/视觉中国
右图:卡若遗址出土的石项饰。图/视觉中国
1985年,经过整理、研究和撰写,《昌都卡若》出版,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部单行本考古报告。看上去,对卡若的探索基本告一段落,但实际上仍有许多问题待解,比如遗址紧邻澜沧江,但当时的发掘中却没有发现鱼类和捕鱼工具的痕迹。
2002年和2012年,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李永宪领队再次对卡若进行探查和发掘,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当年的发掘方法比较粗糙,鱼骨很难发现,报告中只能暂且认为卡若人不吃鱼。但我们通过筛土这样一种方式,从泥土里筛出了很多鱼骨。”
“今天讲考古材料,有一个趋向或者目标叫作‘高分辨率’。这有一点像刑侦破案一样,四十年前没有DNA、没有人脸识别,能够提取到的信息相对有限,现在不仅有DNA、GPS、人脸识别,还有监控、大数据等各种各样的物证学技术,对刑案的判断就会更加准确。考古材料的分析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能获取到的信息增加了许多,能探究的面向也就大有不同了。”李永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拉萨的“半坡遗址”
对于有着拉萨“半坡”之称的曲贡遗址,相关认知同样经历着匡改。
这个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遗址,最早是1984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队员更堆、张建林等人在文物普查中于拉萨北郊娘热山下发现的。由于附近就是村庄和医院,加上长期的水土流失,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但就裸露出来的陶器和石器残片来看,更堆坚信这里埋藏着早期人类生活的痕迹。
经过小规模试掘,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想。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进藏考察,再次确认这是一处少见的高原古文化遗址。于是1990年起,抢救性发掘正式启动,当年曾是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队员的李永宪也参与了发掘工作。
连续三年的努力,考古队收获颇丰。首先,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石器中尤以磨盘、磨棒、石杵和梳形器引人注目。前三种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后一种可能用于编织毛毯,它们共同表明当时曲贡地区的农耕和畜牧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陶器制作则以精美显著,其中绝大多数采用了“磨光暗花技术”装饰器表,工艺特殊而进步。
更加珍贵的是两件动物堆塑,一件为猴面,一件为鸟首。在藏族文化中,猴和鸟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许多藏文史籍中皆有记载,藏西藏北的岩画中则常见对鸟的描绘,有些图像与雍仲、日月、神树等宗教符号组合在一起,甚至处于中心位置,吐蕃王朝之前最为强盛的古“象雄”也以大鹏鸟作为图腾。尽管曲贡遗址的这两件堆塑并不一定与后世信仰直接相关,但绝非随意为之,或许包含着原始宗教艺术的因素。

曲贡遗址晚期墓地内的带柄铜镜
其次,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枚铜镞,是西藏已知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其配料与中原地区早期青铜相同。晚期墓地内另有一件带柄铜镜,造型风格与欧亚草原及北方游牧文化流行的带柄镜比较相似,被视为高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产物。
在动物遗骸方面,有动物骨骸出土的35个探方和16个灰坑中,绝大多数有牦牛的骨骼、牙齿或角心骨,意味着拉萨河谷的原始居民已开始驯养牦牛,而且很可能成群放养,这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有关家养牦牛时代最早的实物材料。
此外,曲贡遗址还呈现出一些特殊的丧葬现象。在一些灰坑中,既有完整的头骨又有专门切割下的头盖骨,并伴有兽骨、陶片、打制石器等,可能与某种随葬的祭祀有关。类似的现象在许多考古材料中都有所反映,中国南方地区乃至东南亚、大洋洲的原始民族中就有猎头祭祀,砍头锯颅的习俗则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而数十座墓葬当中,都采用了“二次葬”或者“屈肢葬”的葬姿,显然是一套成熟的埋葬习俗。
不过,当年的考古在年代框架上将遗址确定为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500年,同时划分为三期:曲贡文化期、曲贡晚期及石室墓期。但时隔三十年之后,2020年四川大学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又做了一次小规模发掘,也重新进行了碳-14测年和贝叶斯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划分出的曲贡文化三个主要堆积时期与以往几乎完全一致,只是主体年代有所差异。因此,新的年代框架定为了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300年,对比原定晚了约500年,且持续时间不足百年。
研究者表示,新的测年表明曲贡文化不仅晚于青藏高原东部出土粟、黍的“卡若文化”诸遗址,也晚于南亚西北部具有相似文化因素的诸遗址,对于认识喜马拉雅南北两侧的史前文化因素传播和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就在于它是不断地通过发现和研究修正原来的结论。”在李永宪看来,曲贡遗址年代的调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它既不说明之前的判断毫无意义,也不代表现在的判断今后不能被修正,未来随着对新发现、新技术的研究,一切也许还会改变。“田野考古永远是对古代曾经完整的事物随机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视窗。就像5000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可能发现、发掘到早年北京城中心或郊县的某个地方,但很显然,他们要全面了解昔日的‘北京市’全貌,仅靠有限的发掘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上:左图:曲贡遗址出土的黄陶罐 图/视觉中国 右图:曲贡遗址出土的穿孔石球 图/视觉中国
下图: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 摄影/本刊记者 徐鹏远
未知与保护
无论曲贡遗址,还是卡若遗址、玛不错遗址,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探索。
今年,玛不错遗址发掘按下了暂停键,考古队需要休息一下,已经掌握的资料也需要好好地整理整理。但过去五年,发掘的面积只不过1%,还有许多未知沉睡在地表之下。比如:遗址中还没有发现房屋遗存,那些在此留下了活动痕迹的人们住在哪里?又比如:那些安葬在此的尸骸是什么关系?他们来自同一个聚落,还是四面八方互不相识的人?各种各样的葬姿是源于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还是别的什么?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玛不错的考古最起码要做10—15年,甚至有可能15年以上。它可以一直做到我退休,如果到时候我还能主持,我就接着去,如果不能,那就换成新的领队。”夏格旺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之类似,曲贡遗址发掘中房屋遗存的缺失,究竟是什么原因?它们是被压在了现代建筑的村落之下,还是根本就不在附近?不管是何种原因,曲贡遗址依然留存有分析研究的巨大空间。
卡若遗址则刚好相反,它有房屋基址,也有石墙、石路、石台基等遗存,却唯独没有发现与遗址同时的墓地,当时生活在卡若村落的人们死后埋葬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丧葬习俗又是怎样的?这同样让西藏的考古学者在想象中充满期待。
当然,考古发掘对完整的研究而言只是来自田野的基础工作。正如李永宪所说:“对考古学来讲,发掘是为了了解遗址所包含的信息。这种了解不是单纯地凭借发掘面积的增大,还在于我们能不能把各种信息条理化、系统化、精确化,并且以某种通行的形式保存下来。这就像医生看病,确诊病情是首要目标,而不是在病人身上不断开刀、解剖来知晓病情。只要遗址发掘所获各种信息是准确、系统的,遗址的价值可以基本评估,完全不必‘斩尽杀绝’,因为保护遗址是第一位的,要给将来的工作留下空间。”
而保护遗址,同样是一道任重而道远的命题。
1982年,侯石柱回过卡若,也是他和遗址最后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水泥厂建在卡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那里的地表有一层做水泥的黏土。1979年我们走的时候,其实跟他们强调了取土不要超过多少厚度,否则会破坏遗址的文化层。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证,结果真就出了问题。然后当地文化部门向我们做了汇报,单位就派我过去,制止挖掘。”1990年,侯石柱被调到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生活转移到北京。
而就在他离开三十年后,水泥厂原有建筑完全拆除了,一座总投资1.2亿元的遗址公园在卡若遗址动工,旨在以遗址展示、模拟考古、场景复原三大主线为基础,建立起一处集文物收藏、展示、利用、研究、教育为一体的新型遗址保护区。2015年公园一期工程完成,并于2019年正式开园,同时二期工程也在2020年全面竣工,不仅成为昌都市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也是西藏地区首个史前遗址公园,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在属地管理部门的规划中,曲贡遗址和玛不错遗址也有建设遗址公园的打算。面对玛不错周边开阔的草场,康马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谢重洲甚至描绘了一个颇为宏大的构想:“遗址那里建起棚子来,游客可以参观、学习,然后外围弄一些马场、靶场之类的,供大家娱乐休闲。”其实对康马县而言,旅游资源并不稀缺,景色优美的崇巴雍错、历史悠久的乃宁寺、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朗巴村等等都在其辖内。谢重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他们最看重的还是玛不错:“文化价值大,文旅文旅,文化在前,旅游在后。”
但遗址公园的建设需要完备的条件,需要充足的投资,也需要满足申请条件和履行程序,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在此之前,日常的看管以及必要的维护仍是基本操作。拉萨市城关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专干次德吉就表示,目前他们聘用了两位管理员对曲贡遗址轮流值守,每年也有专项资金进行除草防火:“去年我们还新修了遗址的围墙,光是这个项目就投入了174万元。”
“对遗址的保护不仅限于现在,更要保护它的未来。我们得给子孙后代留下文化遗产,这对提升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是非常有用处的。”侯石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