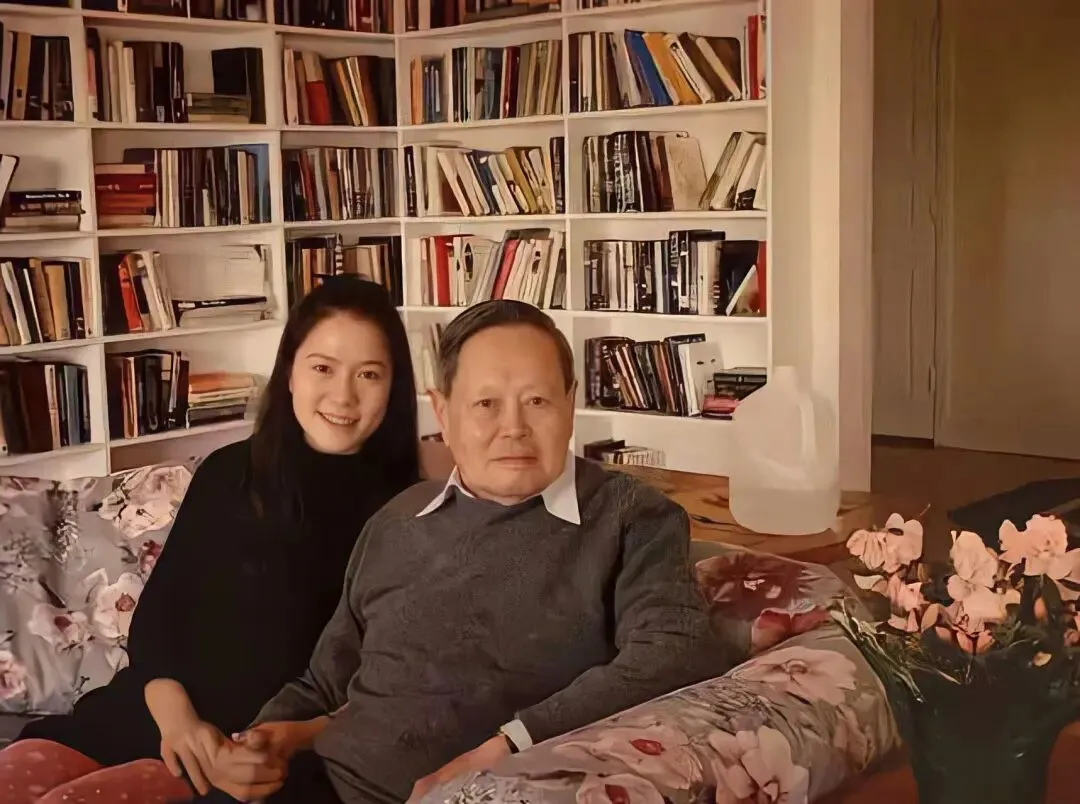儿子返乡带老人体检 心痛父亲的重母亲的轻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很多人的2023,充满了跌宕起伏。春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喘息时刻,既能停下来享受亲情的温暖,也能整顿自己的心情,畅想新年的际遇。同时,这也是一个反思和自省的时刻:我是怎么走到了今天,明天又该如何寻找新的人生可能?
人是环境的产物,又以自主的行动改变着型塑我们的环境。过去的一年,有人转换了工作赛道、生活地点,有人做出买房结婚等重大人生决定,有人想跳出职场去寻找诗和远方,还有人重新认识和至亲的关系。这些选择离不开外在因素的影响,可是也有个体的内在冲动,想去一个有风的地方,感受自由的吹拂。
搜狐“狐度工作室”春节推出特别策划《去有风的地方》。一起来看五个人生境况迥异的人,如何改写日常,追风而行。在他们身上会发现,不管环境如何,人总有抵抗命运的渴求。外界障碍再大,也不能消解人对自由和爱的渴望。
那天凌晨三点钟我被母亲叫醒,一睁眼,床前站着个人,确实叫我直接晕乎了。母亲惊慌不定,爬楼的极速消耗让她快喘不上气来,而我像被强行启动的机器,当时头疼难受整个人懵圈。母亲说,小标,你快去看看,你大(方言父亲的意思)浑身打颤,跟打摆子似的,就要不行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的床,赶紧到他们的卧室。眼前所见,让我晕眩更加厉害。
只见80岁的父亲下身穿着秋裤,上身裹着薄棉袄,刚从卧室角落的坐便器上起来,站在那里无法迈步,面色黄白,进退不能。但他努力地维持不倒,浑身上下每一处都在颤动,从小腿肚到大腿再到腰部,裹紧了棉袄的上半身受到波及,手、头也是剧烈摆动。
我赶紧上前搀扶,几乎半拽着他,让他躺到一米开外的床上。可他又不要盖被子,说是嫌热,盖不了。只是说这几个字,我都能听到他上下牙碰撞的声响。
有几分钟时间,头晕让我感到恶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几天先是母亲重感冒,去村卫生室挂了三天水,情况好转。头天中午,我给父亲测了体温,显示正常,他自个也说没被传染。
我什么也没做,就觉得慌乱,但感觉时间飞快。我跟母亲说,还是打120叫救护车,母亲说好。
1
拨通120,讲了父亲的情况,我问怎么办,接线的人说可能是高烧,我又讲了村里的地址,说了明显的地标超市。我就站在父亲的床脚等着,他依旧在激烈地打颤,好像不由自主地要把自己摇散,看得我十分难受,就觉得露在被子外面、蜷曲着四肢的这个人非常可怜,人怎么可以这样。
县城距离村子15公里,救护车到了村南边的路口,打电话过来,我去开院门,摄像头照明报警启动,我向百米开外的他们挥手。凌晨四点的村庄真黑,被照亮的我估计很亮。正在东张西望的司机一下子看见了,跳上车迅速把车开过来,倒进院子里,卸下简易床。
图文无关,来源,IC photo
难题出现了。父亲这时候已经不抖了,能站立,但完全不能挪步,而他又高又胖,我根本抱不动。我只能用背的,他因为使不上劲,我忙乱中抓住他两个手腕往前挪,因为必须使劲,生怕拽断他手臂。到了下三级台阶的时候,更是难,哪怕日常练很多核心,关键时刻力气还是欠奉。
最后,到底是把沉重的肉身搬上了救护床,我像是凌晨上工的搬运工。
整个过程,随车女护士和男医生,还有司机都站在一旁不搭手。我理解是,他们不敢沾边,万一病患在这个过程中出什么事,比如摔倒出现意外,他们可能怕担责任。
我只记得三十来岁的女护士进厅堂大门,看到柜子上的照片嘀咕了一句:这家好多照片,拍得不错。
上车后,医生问我去哪个医院,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县中医院的救护车。我说去县人民医院急诊,他们确认了两遍,我坚持了这个目的地,他们没有再问了。启动,发车。护士给父亲戴上了吸氧面罩,父亲拨弄到一边,护士也没再管。量了体温,38度多,略显空荡的车厢内,也没什么能做的。漫长的路上,我只觉得冷,护士关上了窗户,开具了费用,用POS机刷了230元,给了张很大的红纸收据。
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没什么人,值班护士似乎正在交班。一番折腾下来,抽血验血,我拿化验单给年轻的男医生看,他说从指标看是感染,但具体是什么感染,他也说不清楚。那就挂水消炎吧,我说好。
在交完费取急诊药之前,我看到躺在移动铁床上的父亲有异样,发现他裤子湿了。我说,你要是想上厕所,告诉我就行。父亲带着委屈回,我哪里知道?好在上救护车时,母亲塞了一套换洗的内外衣裤给我,母亲像是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把车推到医院一处灯光昏暗的地方,扯下父亲的外裤内裤,他不能动弹,所以只好用扯。我再用纸巾擦拭干净,没法清洗,只能算是不脏了吧。天亮之前的县医院,没有人走动,安静得很。这是我第一次给父亲换衣服,全程下来,他嘴角似乎凝固着不失尴尬的微表情。我很像是给一长溜硕大的人形肉块脱衣服穿衣服,我边换边嘴欠,对不能还嘴的父亲说着少量的怨言。
在那个我怎么也不愿意去熟悉的冰冷医院里,我确定无疑地知道,这是我暂时不能自理的父亲,我不可能置身事外。
2
期间,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过来站在一步开外,盯着我。我问他是谁,为啥一个人在这黑黢黢的地方,他说着不太连贯的本地另一种方言,大意是要来做检查,还问有些癌症是不是可以治疗。我敷衍着他,说大概是这样。
清理完父亲的脏衣服,我推着他到急诊输液室报到,再找一处联排椅子让他躺下插上针头,没一会,整座医院像苏醒一样,驱使更多男女老少挤进这里,护士更多了,但交药和插针的柜台前还是得排队,原本宽敞的输液室很快坐满了病人和家属。
没人靠近我们,无论是尊重还是嫌弃。
图文无关,来源,IC photo
这次进急诊,是父亲在数月间的第四回,前几次都由二姑家表弟或二姐外甥女送到医院,这次赶上我亲力亲为。父亲在三年前遭遇车祸,头部受伤,他原本不错的身体每况愈下。被鉴定伤残十级的父亲,自行散步的距离从车祸前的一两公里,缩短到二三十米,即使这样还会出现莫名的脚软,偶尔出现小便失禁。
正常的步态已经从父亲的人生里消失,他走路时膝盖弯曲,只能拖着脚摩擦地面前移,经常会直直地扑倒在地。
我猜测,车祸导致父亲脑干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后遗症至今都没被身体吸收,一定产生了无法确切知晓的体内改变,合并他的高血压与糖尿病,每次去医院都检出强烈的感染指征,可县市两级医生都无法准确给出诊断结论。
我很担心父亲摔断手脚。有一次,我说你在意识到要摔倒前,可以立即蹲下来。父亲对这种高高在上的指导明显有抵触,他用反问句式,同样说在摔倒前他根本没法控制自己。这时候,我就知道哪怕是父与子,对于衰老与病痛也无法真正交流。感同身受这回事,恐怕只是说话者的礼貌用语。
3
我每次呆在老家,总会在乡音恢复得刚刚顺溜时就离开。所以,父亲养病的最大优势,以及他能不能消除对84岁的恐惧(参见“73、84阎王爷不请自去”的谚语),肯定不在于有我这个小儿子,也不在于一家生活在国外的大儿子,或者自顾不暇的大姐二姐,完完全全在于有母亲的照料。
父亲车祸之后,母亲最大的改变,也许是她接管了父亲的退休金,成了每月3000多块钱的主人,是当月即取,还是攒几个月支取,她是话事人。虽然这仅仅是形式上的,毕竟钱大多花在父亲身上,并且还要承受他越来越糟糕的脾气,可是对母亲来说,这也许是重要的形式主义吧。
母亲除了类风湿导致的腿疼,其他都好,翻看摄像头录像资料,我发现她总是骑着她的三轮自行车进进出出,一刻也不消停,哪怕是坐在那,要么是择菜,要么是烙饼,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
去年十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可能太过注重父亲的健康,忽略了母亲的身体,于是带他们俩一块去县中医院体检——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他们听邻居说,这里看病很快,不用等整个上午或下午。
实际经历表明,它的速度确实比县人民医院快,但医生形同木偶,动作迟缓,用不知所谓的惜字如金,掩饰他的不明所以。
这次检查肾功能需要验尿,父亲站在小便池前十几分钟没有成功,不忍让他坚持,只好作罢。等我回头再去领母亲抽血,利用了老人优先的便利,插队抽血,但男护士扎了两针,找不到母亲的血管,捏着针头到处探查。
我让他换人扎针,换了个走来走去忙活的女护士,一扎即中,血涌让包括围观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说是节省时间,其实也是枉然。一切搞完已是晚间。我先把父亲搀到车上坐定,再去接母亲。回程的路上光照并不好,几十年来,她绝无仅有地主动拉住我的手,是攥紧了的那种力道;而我忘记了收慢步速,母亲终于跟不上,在过停车场一处很低的坎时,她绊倒了。电光火石的瞬间,我条件反射地去捞她,双手抓住她的厚衣服将她背朝上拎起来,一刹那的痛感,母亲真的很轻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