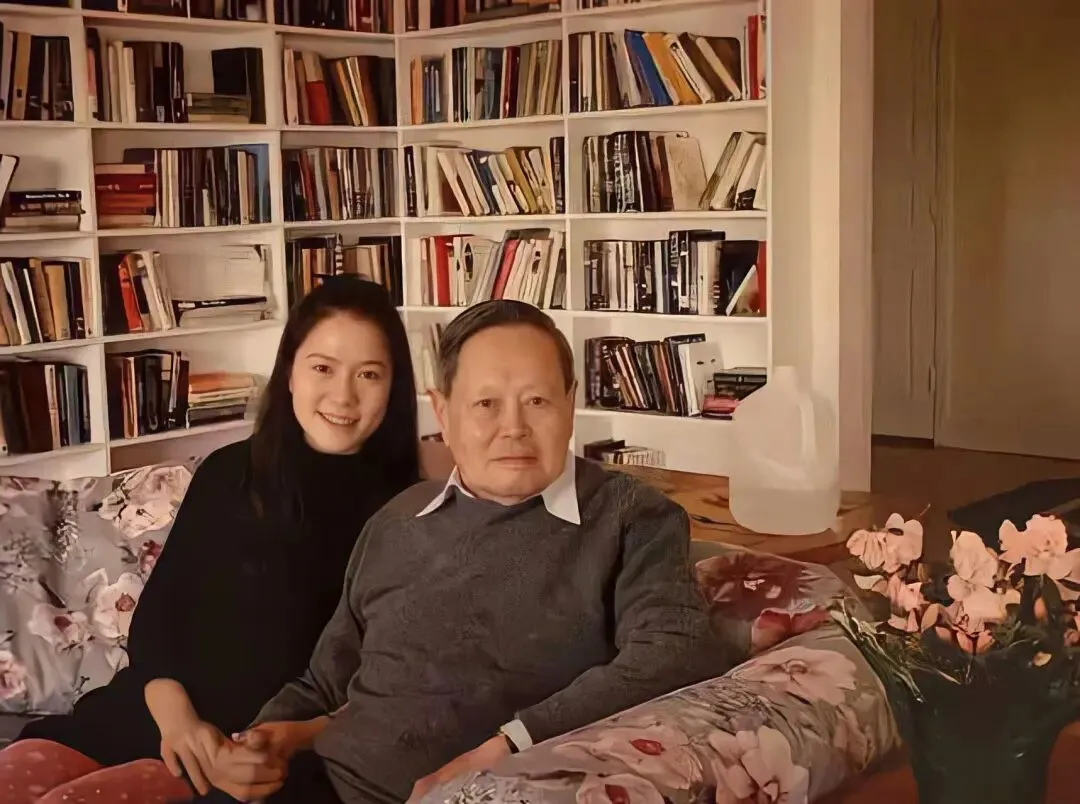男子做临终关怀志愿者4年 曾被绝症老人骂滚出去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你跟女儿讨论过死亡吗?”话问出口,在安宁病房做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张明义,亲眼目睹了一个成年人崩溃的瞬间。
五十多岁的老秦,在癌症晚期选择放弃治疗,住进了安宁病房。“不想做化疗了,太贵了,也太痛了,顺其自然吧”,老秦告诉常来陪自己聊天的张明义:“我跟医生说了很多次给我多开一点安眠药,让我可以明天不再醒过来。”张明义想问问他有没有和女儿交流过死亡,老秦却突然眼眶一红,嚎啕大哭起来。
“直到他去世,父女两个都没有坦诚面对过这个话题”,张明义有些唏嘘。
“人生会遇到很多坎坷,有些能够迈过去,有些却不能。”在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的四年里,张明义陪护过很多病人,也作为发起人举办过多期“死亡咖啡馆”活动。张明义觉得,如果我们无法直面死亡这个问题,就很难舒适、安静、安详地去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也无法死得体面。
被忽视的病人心理健康
广州一间社区医院的安宁病房,空气里总是有一股浓浓的药水味,和一缕陈旧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被放置得久了,没有生气。
住进这里的人,通常已经被医生判定了死刑:生命只剩下不超过6个月。但也不绝对,张明义见过许多老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几年。
工作太忙,距离上次见到薛大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张明义再次来到医院时,发现那张19号病床上,已经躺上了另外一个病人。
安宁病房的床位,空了总是很快就有人补上。短暂的伤感过后,张明义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情,转向隔壁病床上,那位一口潮汕话和福佬话混杂的老大爷,开始陪他拉家常。
见有人来跟自己聊天,老人好像突然来了精神,絮絮叨叨讲起自己的过往。方言有些晦涩,张明义听懂了不到十分之一,只能不断微笑着点头附和。断断续续,张明义听明白了老人的一些抱怨,在病房里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儿子来探病,不让他多说话,说多了更是会斥责他。
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老大爷不停嘴的说了多半个小时,直到开始有点喘息。张明义起身倒了杯水递过去,老人慢慢停下来,望着他的眼睛,换成了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说得很爽,很久没有这么说话了。”
闲聊间,老人的儿子带着孙子前来探病。张明义坐在一边安静的听着父子间的交流,几乎都是关于吃药喝水和如何护理的叮嘱,以及父子之间事务性的闲谈,话说完之后,病床前陷入了短暂且尴尬的寂静。
张明义试图告诉家属,病床上的老人更需要心理安慰和关怀,满脸疲惫的儿子有些无奈:“我用尽全力,也只能维持家庭与父亲的赡养和护理,哪有时间再去关心他的心理健不健康,会不会寂寞无聊,身体能吃得消就不错了。”
张明义默然。
“别怕,有我们陪着你”
临终关怀究竟要做什么?
“并不像某些外界流传的那样神秘”,张明义说。所谓临终关怀,需要由医生、护士、社工甚至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等多方人员参与,对一些病人进行姑息治疗和心理疗护。
作为志愿者,张明义认为自己从操作层面上能做的其实简单且平常。“陪着安宁病房的病人聊天,给他们按按摩,放松肌肉;如果是一些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的病人,那就陪他们发发呆。 ”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这是美国医生特鲁多墓碑上的一句名言。
临终关怀志愿者雨晴曾陪伴过一位乳腺癌晚期的女人。
为了照料,病人的丈夫和女儿每天轮流在病房里陪护。
躺在病床上的女人非常焦躁,上一分钟嚷嚷着热了,下一分钟就喊着渴了,总是静不下来。雨晴带着志愿者去陪护的两个小时,大概是父女两个一天中唯一能够休息的时间。
志愿者的陪护,起初女人并不理睬,大部分时间都不愿意开口说话。雨晴没有勉强,一直安静的在床前陪着,偶尔为她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突然有一天,病床上的女人示意要纸笔,雨晴找来递给她。
“我很怕死。”女人颤抖着写下了这几个字。
雨晴有些懵了,停了一会,用笔写道:“我也怕死,我们都会死。”
“我不想死。”女人又写。
握着女人枯瘦的手,雨晴慢慢凑到她的耳边,轻轻地说“别怕,有我们陪着你”。
女人不说话了,默默地放下纸,说要睡一会。她安静地睡了一小时。
几天之后,雨晴收到了她女儿的短信说,“我妈妈走了,走得很安详。”
后来雨晴才知道,家属一直不愿意告诉女人病况。“或许因为如此,她之前才总显得非常急躁不安,因为人越忌讳死亡,对它越一无所知,恐惧就会越大”,雨晴觉得。
“很多家属往往会选择隐瞒病情”。在陪伴过程中张明义发现,多数绝症患者得知自己的病情时,通常会经历愤怒、否定、沉默、配合这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心理护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临终关怀之中的陪伴环节能给予的,恰恰是有时医护及家属不愿去触碰的那部分情感上的安慰。虽然不多,但或许足以让处于生命倒计时中的患者,生出一些面对死亡的勇气”,张明义说。
“要学会接受你的没用”
“你要学会接受,你做的事情可能完全没有用”。
张明义始终记得自己第一次陪伴的病人,是位已经躺在病床上两年的老人。疾病让他无法行动,说不出话来,也很少有家属来看望。张明义每次去,会给他擦拭和按摩放松,有时就坐在床头跟老人闲谈。
“你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他是开心的。”
但更多时候,病人的不配合是常态。
一位老人因为无法正常进食,只能通过塑料管把营养输进身体。老人觉得管道弄得他很不舒服,背着人,悄悄拜托张明义帮他把管子拔掉,张明义拒绝了。老人非常的生气,尖叫大骂着让张明义滚出去。
面对这个暴怒的老人,张明义第一次内心涌起了深深的伤心和无力感,来陪伴老人家,为什么却连他的最后一点点请求都帮助不了,还无法缓解他的痛苦。
张明义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临终陪伴,究竟有没有意义?
同样的经历也存在于另一个志愿者梁君(化名)身上。在第5次去陪护那个患了脑瘤的13岁小女孩时,他兴冲冲带去了她喜欢的许嵩海报,却得知小女孩去世了,已经被送往医院准备摘除和捐献器官。
“我本来准备了惊喜,却瞬间有一种希望落空的感觉。有那么几分钟,我怀疑我做的这一切是否值得。”梁君说。
最终张明义想通了,“人不可能做好每一件事”,但他开始为自己陪护的病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为他们带一颗家乡口味的椰子糖、写一张明信片、唱一首歌,陪他们聊聊自己的过去……
“你会发现面对陌生人,病人反而更愿意倾诉。有一些老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会想和孩子聊后事,聊一些心里话,但是孩子每次都把话题岔开,‘你会好的,会长命百岁’。“
“如果有下辈子,我想当个哲学家”,曾是高级工程师的薛大爷,病到无法起身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跟张明义闲聊,含糊的声音里透出了一丝眷恋与不舍。这些话,薛大爷没有告诉过自己的儿子。
走进“死亡咖啡馆”
“很多情况下,这个时代在屏蔽死亡。我们需要一个场合,能自由谈论死亡。”
在接触到“死亡咖啡馆”概念后,2018年前后张明义发起了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召集一群人舒适的围坐在咖啡馆或茶馆,吃着甜点,谈论生死。
这种让参与者在舒适氛围中诉说自己对死亡的经历、见闻、看法的活动形式,被称为“死亡咖啡馆”。2011年9月,英国人Jon Underwood在家中组织了第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此后,死亡咖啡馆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迅速蔓延;2014年,两位从事临终关怀领域的公益人将死亡咖啡馆这一形式带入了中国。
张明义举办的第一场活动,报名的有70多个人。他有点震惊,居然有这么多人对“谈论死亡”感兴趣。
每次活动,张明义都会设置一个环节,“假如你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你将会做什么?”
有参与者说,想要听听大家怎么夸夸自己。西方的告别会上总是会有亲友说悼念词,时不时有夸奖与回忆中的笑点,但是东方的葬礼却并不存在这样的环节。所以她想要在死亡之前,听听大家会如何夸奖她。
也有参与者说,会去跟所有曾经暗恋过的男生,一一告白,然后努力去谈一场认认真真的恋爱。
有人说,在跟所有人告别之后,想要在爱人的陪伴下走到最后,不想要在冰冷的病房里,等待死亡。
也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想要试着找找身边的人,看看谁能在她走后,可以帮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但在分享的那一刻,才突然发现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人。
更多场参与者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年幼时期经历父亲去世的女孩颤抖着讲出了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和阴霾;急诊科医生迫切的将自己每日接触死亡的压力在这里一吐为快。
有故事的人多数都带着伤痛,而这些分享者几乎无一例外会嚎啕大哭。张明义能够体会参与者的压力、抑郁或者痛苦,更能感受到他们希望从这里寻求帮助的期待。
“我会建议他们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交流”,作为活动发起者,张明义从来不会刻意去满足这些期待。“死亡咖啡馆只能提供一个场所,让参与者自由倾诉,尽情交流,作为组织者给予的只有流程引导,必要时提供一些问题让大家进行思维碰撞。”
但他能感觉到,很多人诉说之后身心的放松。
某次在活动快结束时,有人提了个问题,“如果一直参与临终关怀的公益,和这样放开谈论死亡,会不会让人对生活失去期待”。
“我认为不会”。作为组织者,张明义很少发言,多数时刻他都在尽力倾听。一个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让他愈发意识到生的时间有限、死的降临无常。
“正因为理解得更透彻,才会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张明义觉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田蓉曾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临终关怀社会支持研究》一文中写到,在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中,临终关怀社会工作的开展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城市,专门以临终关怀为核心业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更是寥寥无几。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1.9亿,占总人口的13.21%,相比2010年提高4.63百个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46%;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安宁疗护(临终关怀)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如何让临终患者安宁、舒适、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时光,如何教会人们正确认识死亡、思考死亡,是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象征。”
“但这些话对我来说还是太大了”,张明义说,“我只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一些人,能让一些人意识到临终关怀是必要的,就足够了”。